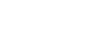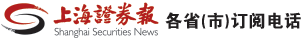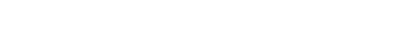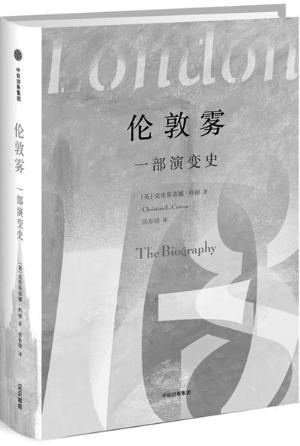伦敦为治理漫天雾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 ||
|
——读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
⊙刘英团
对雾霾之害,国人如今也有了切肤之痛。其实,“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形,当今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的伦敦大雾。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狄更斯名著《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描述的那样,这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在狄更斯笔下,这是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剑桥狄更斯学会创始人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 L. Corton)在《伦敦雾》中,巧妙地结合历史和文学的敏感性,全景式地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
雾霾,使人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窒息感
“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1873年,神智论者(theosophist)爱德华·梅特兰(Edward Maitland)从未来的角度回顾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如今,你看到我们宽敞整洁的房屋,装修雅致,亲密而有序地坐落在一起,就会想起过去的岁月:那时候,鸟儿飞过城镇上空都会被窒息感所挫败;那时候,每座房子都是一座火山,每根烟囱都是一个火山口;它们永不停息地喷发着火光和浓烟,把天空染成华丽而颓废的颜色,注满了黑暗和毒气。”科顿认为。对很多作家来说,雾“成了一种消除社会秩序的分层体系的象征,它模糊了道德界限、用朦胧和怀疑来代替确认和肯定”,“被犯罪和侦探小说家们简单粗暴地当作神秘和黑暗事物的符号。”在文坛大家如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大量迷人却被遗忘的通俗文学,以及克劳德·莫奈等画家的画作中,雾引起了“社会危机、不道德、犯罪和无序”。
“雾霾是无形的”,然而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画家们、音乐家们却从“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至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并通过“隐喻的雾”来表达某种道德、心理和社会“情绪”。“伦敦雾”还折射出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烟尘弥漫甚至被那个时代的不少人视为“是进步、成功和经济繁荣的标志”。在《伦敦雾》中,记录了《泰晤士报》的一句“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使人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窒息感。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哀叹伦敦雾的“恶臭和阴暗”,更早时候的德国作曲家海顿发现,伦敦的雾霾已严重到“可以将它撒在面包上”的程度。而科顿则感叹:“当时的雾非常大,家长们都被建议不要送孩子上学,因为很可能在路上走失。”“在昏黄的街头,‘linklighters’(即提着自制手电筒的流浪儿提供有偿带路服务),不幸的有钱人会被诱骗到深巷里,惨遭抢劫”,这又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在《杰出城市的厄运》中,威廉·迪莱尔·哈伊更精准地预见了有毒的空气令大批市民窒息而死的惨况。
穹顶之下,恐慌与雾霾一样无处不在,且不可避免。“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伦敦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一度降到了零,人们甚至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公路和泰晤士河水路交通因此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由于浓雾,只有寥寥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演讲厅,却几乎看不见台上的马克·吐温,以致这位以幽默著称的作家不得不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在《伦敦雾》中,科顿不但系统地跟踪了雾霾这种现象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还“使用雾霭弥漫的形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在科幻小说中,浓雾俨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罗伯特·巴尔在《伦敦的厄运》里形象地将致命的大雾比喻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垫子,向整个城市压下来。”狄更斯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用雾来隐喻因金钱欲望导致的道德腐败,将其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
“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
工业革命的兴起,让伦敦城市发展迈上了快车道。由于当时工厂多建在市内,加之居民家庭争相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暴增,遂使“伦敦有如地狱,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珀西·比希·雪莱语)。1921年,伦敦每立方英寸样本的空气中含有34万煤烟颗粒。在《伦敦雾》中,科顿梳理了十九世纪以来英国人在报章、文学、词典、绘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所谈到的伦敦雾,勾勒出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他们将雾称作“伦敦特色”,既“体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属性,一种首都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但也包含着反讽意味”。一方面,“雾已经变成了伦敦本身,还夺去了伦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变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这座城市将自己隐匿在大雾中,试图挫败每一个冒险者,制造混乱和痛苦”。另一方面,“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W·P.伦德语)。所以,“伦敦人宁愿呼吸碳、灰尘、水汽混合的浓浆,被呛个半死,也不愿处理他们生产的烟尘”(杰克逊·雷语)。
“我们有雾蒙蒙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堆丰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话语。”科顿感叹,以伦敦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大多数的人把雾霾当作生活的组成部分,顶多算一种“麻烦讨厌的事”。当然,也不乏先知者把雾霾作为没落的象征或隐喻。在作家伊夫琳·沃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中,雾的消退就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象征:“雾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认同了这副样子。”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借用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的“煤炭城”(Coketown),来反思雾霾之祸,认为“这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经济体”。物极必反,伦敦雾又是环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空气清洁法》的出台,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真正走上了一条治理空气污染的大道。流行病学专家德芙拉·戴维斯认为,英国人在饱尝了因烟雾毒魔对生命的大量吞噬而带来的恐惧之后,不得不痛定思痛,汲取无数生命换来的教训。
在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后,英国政府正式向空气污染宣战。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内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煤烟污染的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往郊外”。1968年,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如果绿色植物都被杀死,那么空气中的氧气也会迅速消失。”长期呼吁净化空气的白金汉区议员、出版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多次向议会提交与前工党同事鲍勃·爱德华兹相似的法案。法案不但要求加强对颗粒排放物和烟囱高度的限制,还给予内阁足够的权力去引导、督促地方政府尽快根除污染。英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毫不含糊地写道:“新一届政府,不论其政治构成为何,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立即采取行动。”
然而,推行这些法令并不易。按《清洁空气法》,英国环境部负责控制注册工厂的排放物,而地方政府控制其他非注册领域的排放物。中央与地方争夺企业管辖区,为法令落实留下了缝隙。民众虽是空气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但出于利益考虑,也会反对政府的一些环保举措。比如矿工原本可免费获得分派的烟煤,一旦改用无烟煤,他们就要多一笔使用无烟煤的开支。改造供暖设备,除中央拨款外,地方政府和户主还要支付约30%的成本。几经努力,至1975年,伦敦每年的雾日降到了15天,1980年更降到5天。
治霾依然是世界性难题
当然,治理空气污染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那些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针对雾霾,有人提出“后工业社会”,有人提出“去工业化”,而科顿则认为:“法律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去落实它。”正如威廉·里士满爵士在给《泰晤士报》的第一封信中所言,空气污染之下,无人可做看客。食品能“特供”,空气和整体生态环境却不会区分何人居庙堂、何人处江湖。治理污染,我们既要继续向上,实现产业升级,更要政府主导强力控污。
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阀值,生态平衡就变得不可逆转,再治理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伦敦雾》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英国的治霾实践更告诉世人,污染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副产品,而严苛的环境政策也并未使经济恶化、社会倒退,政府收入也没有因为治霾治污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