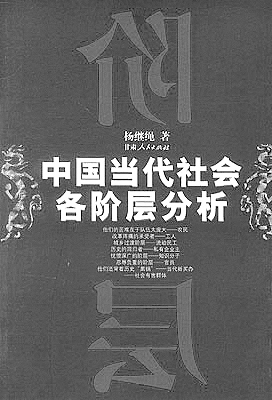|
杨继绳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敢说真话,在我所敬重的人中间,他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他的《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很好读,内容丰富翔实,行文明快犀利,非新闻高手不能为。与同类著作相比,杨著最可观之处还是一个“真”字。首先是真实,记实是全书的主体,他自己说是想“介绍有关社会阶层的一些情况,”以我的阅读所及,这个“介绍”全是干货,不掺水分。比如关于农民和工人两大群体社会地位、利益处境的演变,如何从国家主人和国体的基础,变成今天高度边缘化的弱势人群,整个过程的叙述让人刻骨铭心。其次是真知,杨先生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情况的分析,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可略引数段为证:
其一,“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机制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
其二,“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是扭曲的:改革受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极其亲属和朋友,改革受益较少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其三,“市场经济的惟利是图和‘审批权力’的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形成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
其四,“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对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说别的,仅凭上述识见,花36元买杨先生的书就值。
再有就是真情。杨先生的真实、真知、真话。反映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这种真情蕴涵全书而溢于言表,令人心潮起伏,热血上涌。
好书总会引起读者对它更多的希冀与期待,杨著当然不例外。全书介绍了九个阶层的情况,其中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官员的定位标准是:“他们的苦难在于队伍太庞大———农民;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这样的定位也许是反复思之的结果,但从道理上、事实上、逻辑上看,难以成立。
为什么人多了,就会苦难?生活中的事实是人多势众,人多为王,民主制度就是人多的那边说了算,尽管也必须尊重人少的那一边的权利与利益。不错,在中国确实有相当一批所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鼓吹农民的苦难在于他们人太多,这些人从马尔萨斯那里取用了最烂的糟粕而不自知,我怎么也不明白,杨先生会受他们的影响。试试让农民自己作主,看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苦难!不仅农民这样,任何一个群体、阶层,人多也好,人少也罢,只要不能自己作主,只要身不由己地被人“运动”、忽悠,都只能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说工人是改革阵痛的承受者,这个“阵痛”的时间未免太长了,用“阵痛”来比喻工人所受的的苦难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工人已经痛了快30年了,不光是生活的痛,身体的痛,而是彻骨彻心的痛。是由九霄之上跌到边缘群体、弱势人群的痛。
说当代中国的4000万知识分子依然是一个忧愤深广的阶层,大概在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几个人会同意。有人计算现在至少有1000万知识分子忙于致富,他们即使有那份忧愤的心,也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忧愤。其实,不管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想发财,多少人想做官,多少人既想发财又想做官,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碎片化。清华大学孙立平先生曾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上层雾头化和下层碎片化的见解,在下层碎片化中,知识分子阶层遥遥领先。
说官员阶层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这是离事实最远的童话。官员的地位、待遇、工作、生活、精神状态,哪点与“辱”“重”连得起来?现在报考公务员的人这么多,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去忍辱负重,那中国何止是现代化,早就成了伊甸园了。“忍辱负重”几个字放在工人、农民(包括农民工)这两个阶层头上才合适,当代中国还有比他们更受辱、更负重的吗?
迄今为止,近几年关于阶层研究的著作与论文和主流媒体对阶层研究的宗旨,都定位在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杨著也是这样。这没有错。但稳定与和谐为了什么?是为了能使各个阶层的人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权力,有按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不明确这个最终目的,稳定、和谐云云不但不着边际,而且面目可疑。能否真的以人为本,把使每个人活得像个人作为阶层研究的终极目的,不但决定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稳定———是传统封建社会的那种超稳态的稳定还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宪政稳定,什么样的和谐———压制一切差异的和谐还是百家争鸣的和谐,而且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走向稳定与和谐。比如,杨先生提出的促进阶层和谐之道是救助下层,制约上层。那么,谁来救助下层,人家不愿救助怎么办;谁来制约上层?靠下层,凭什么?能制约上层的下层还需要上层救助?靠上层自己制约自己,可能吗?其实,在以人治为特征的旧体制中怎样转圈,也不会有通向阶层和谐的道路。这一点,毛泽东1945年7月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话”中就已明示,它就是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