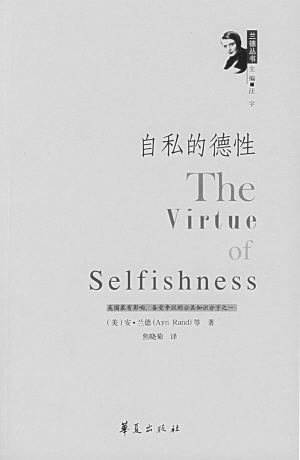|
人应当关心、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美德。
这样的道德箴言,听起来的确惊世骇俗。这样的教诲出自一位女人之口,尤其令人震惊。她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俄国革命时期逃亡到美国,并且很快就成为自由市场及其伦理基础最为坚定的辩护者,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她就是安·兰德(Ayn Land)。
听起来,这似乎是中国民间社会久已流传的格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假如是这样的话,兰德就根本算不上是哲学家了。实际上,当兰德谈到自私的时候,对自私的主体———个人,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
兰德会追问:你所以为的利益,真的是你自己的正确的利益吗?她说:“正如人不能通过任何随意的方式生存下去,而必须发现和实践其生存所需的原则,同样,人的私利也不能取决于盲目的欲望或者随意的奇想,而必须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找到和实现私利”。
自私成为美德的前提是理性。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她的这种伦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古希腊伦理学特征,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都非常强调理智、理性在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会有真即是善的格言。当然,兰德是一个个性十分强烈的人物,她可能从来没有明白地说出自己的伦理学历史渊源。
但是,兰德这样的自私观让普通人有点沮丧。一个人首先得是一个具备十分清醒、有能力认识到客观真理的理性人,才有资格宣称自己知道怎样自私。要做一个真正自私的人,必须十分理性地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并且始终理性地选择。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如果达不到兰德所设想的那种程度,他大约就不配谈论自私。一个人一旦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让自己的行为受某种盲目的欲望或奇思怪想支配,那这个人的自私就一点都没有美德可言了。
应当说,兰德坚持了启蒙运动(即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人的理性能力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她坚信,人的理性是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的,是可以分辨出自己的行为之好坏、对错的。
但是,这样的信念,很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依据常识就可以知道,大多数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即使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十分出色,也未必能够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
举个例子: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企业家基于理性计算发现,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简单方法,就是贿买管制官员,获得对于该规则的豁免权。但,这能够算兰德所说的合乎美德的自私吗?
很难。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规则本身,相反,假如所有企业家都机灵地选择这种策略,那很可能使这项不合理的规则永久化,甚至官员索要的贿金数额会提高。这一结果显然有损于企业家的自私。那么,企业家当初选择贿买官员,是理性的吗?
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十分常见,它十分清楚地显示了“理性”在个人选择过程中的局限性。仅靠个体的理性计算,未必能够保证个人做出“正确的自私”决策。因为,个体的理性计算能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相反,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宗教、道德教化会发挥十分重要的功能。
还是回到上面说到的故事:假如企业家接受了某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告诉他,自由地从事某种活动乃是自己的自然权利,贿赂官员的行为本身是不正确的,那么,大多数企业家就会把这种应对策略排除在策略选项集之外。由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另外的策略,比如,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抗争,通过司法、政治等途径,要求废除这种不合理的规则。
这种策略看起来难度更大,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较小,而且,即使成功,也必然会有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不过,假如企业家的信仰给了他以道德勇气,那他就可能选择这种短期看起来不合理的策略。当然,这种策略最终的结果将会十分可取,至少个人免除了日益沉重的贿金负担,更不要说,整个企业界都因此而获得了正的外部性。
由此可见,企业家的信仰及信仰中所包含的道德约束,其实大大地拉长了企业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时间尺度,甚至改变了他计算的方程,从而使他的决策从长远来看,对于自己的利益来说,更为正确。因此,很多学者说,在道德、宗教信仰、习俗中,其实包含着超越个体理智能力的智慧,这些智慧使得个人不需要思考,即可选择对个人的长远利益来说最为有利的策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
当然,兰德所说的理性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殊途同归:它们都是要解决利己而不损人的伦理难题。只不过,两者的解决进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