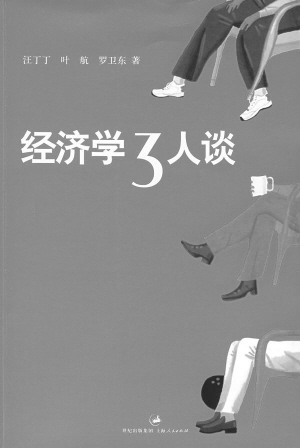|
我在汪丁丁教授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曾多次聆听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三位教授的对谈,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总是让人振奋。现在看着这多次谈话辑集成书,重温一遍,很多谈话情景就仿佛在眼前。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
汪丁丁倡导“跨学科”研究,在浙江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本《经济学3人谈》的一大主题正是“跨学科”。三位学者的知识和兴趣都极广,大略地概括,叶航偏向科学技术,罗卫东偏向历史思想,汪丁丁则对人文与科学都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三位都出身于经济学,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做着经济学研究。从三位谈话的倾向看,显然已经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更新颖的演化博弈论或者“神经元经济学“。对跨学科的倡导者而言,这种趋同的倾向是值得警惕的。
经济学内部有一个不好听的词:“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有些人批评诺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方法,他把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套用到犯罪、家庭、婚姻、教育、上瘾行为、时间分配等诸多领域。贝克尔也被聘为社会学教授,但很难把他称作是“跨学科研究学者”,他的研究领域确实跨越很多学科,可是研究方法和手段却完全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半步都没有跨出去。
所以,若单纯看三位学者的讨论涉及哪些学科或者哪些工具,意义并不大。当然,讨论中确实涉及到经济学、演化理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思想史、认知科学以及古人类学等,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同样可以批评三位学者的诸多盲区,研究中国本土性质的社会科学时,完全没有涉及电影、建筑、历史、文学、美术、音乐或者广义上的文化研究,无疑也就漏掉很多至关重要的思想。
其实涉及学科多少,跨度范围,对界定“跨学科”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如果作者或者对话者缺乏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那么对话就不可能是“跨学科”的,充其量“帝国主义”而已。
汪丁丁教授思考过跨学科中心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个人理性的本质与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实践。前者由认知科学扩展到博弈论,给经济学奠定一个符合逻辑的微观基础;后者以制度经济学和它所蕴含的文化、社会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乃至世界给出一个符合历史经验的宏观描述。前者精细到极致,后者广大到无穷,中间再掺以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等进行人文思想和道德实践的补充,从而构成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框架。
经济学在这套框架里起着支柱的作用,其他学科只是补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怀疑这套框架的“跨学科性”。理性支撑的认识框架只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很多被认为有“碎片化倾向”的学科范式就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框架。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问题。那至少是一件很可怕、很激烈的事情。康德在《系科之争》中已经表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层次的高下,各自要为了这种结构展开殊死的拼搏,现代学科之间的关系不是互补,而是斗争。目前颇有些学者打着跨学科研究的旗帜,只是移用别人一些结论,或者一个基本模型框架,甚至只是撷取只言片语,完全不顾其他系统的基础和前提假设,这种研究只是“帝国主义”式的研究,也是“叶公好龙”式的研究。
有人爱引柏拉图,却不愿学希腊文;有人竭力倡导儒学,却不愿读四书五经;中国学术界或者思想界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卢曼说,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整套自我封闭的子系统,互动作用起来,才构成一个大系统。我们在跨学科地引用一个学者思想或者利用一种学术思想时,手里要提起来的是这个学科整个的学术传统,分量极沉重,非大师不能为。
正如三位教授对话中所暗示的那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很多缺陷,步入很多误区。发展的道路不能只是向前看。一方面要向旁边看,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要向后看,重新认识古典经济学中被人忽视的价值。可是要“跨学科”地研究古典经济学,就不能完全采用现代分工细化的办法来做,否则穷尽一生也未必能把斯密钻研透彻。要知道,斯密也不是用我们现代学术方法来治其学问的。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不及探究斯密思想细节,无力全面细勘文本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斯密?
不同的解读方法产生了许多学术流派。有些人认为,我们就应该精读极少数经典,对这些大师的智慧给予最大程度的信任。我们应有自信,对这些文本进行足够深入的挖掘,可以得到对世界近乎整全的认识框架。可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经典依附于时代。我们在阅读经典时,必须重视它的背景,作者的生平背景、学术经历、交游往来等等。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而不是作者。
无论哪种解读,都必然牵扯出极大的阅读量。当我们介入一个新领域,谈论一个新思想时,要么对这种思想的内涵本身有极深刻研究,要么对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和边界有最全面的把握,这两种“跨学科”研究的路径都对研究者构成重大考验。
几位教授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书里已经讨论得很透彻,既不想取消学科分工,也不想用某些学科压倒其他学科,只是为了探求包容性更好、解释力更强的学术范式。事实上,很多种学术思想都在不同维度上做着努力,但是它们往往互相冲突。
如果单从这本书的多处结论来看,我不认为三位学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演化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思想史,再加上神经元经济学,每一种理论都不足以全面解释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显示,而三位学者也没有做到把它们有机地糅合起来,变成全套逻辑一致的新产品。但是从古希腊对话体的意义来看,我对三位学者的努力充满敬意。我们大可不必从书里寻求什么跨学科研究的答案,对话的意义,必定就在对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