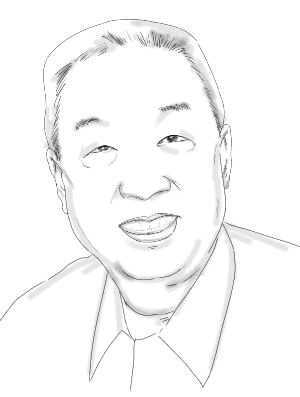|
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辈子不知理财为何物。并非我笨,实在是我的经历使然。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我生长在贫瘠闭塞的农村,难得有钱,也极少用钱。过日子所需的衣食用具都是自家产的,甚至敲石取火,连火柴也不买。敲石能取火,你信不?山东农村,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这绝活。难得有钱、用钱,自然也就无财可理了。
敌人想钱,我们不想钱,我们胜了
青少年时期我当了八路。其实就是一帮被鬼子的烧杀抢掠“逼上梁山”,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用 “小米加步枪”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有着飞机大炮的中外敌人拼杀,看起来很像是“鸡蛋撞石头”,但鸡蛋最终却撞碎了石头——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后来的美国佬,都被我们这“鸡蛋”撞得头破血流,你说怪不怪?
我想,其中奥妙和“钱”有关:敌人想钱,抢财物,甚至为此杀人放火;而我们不想钱,还专打那些想钱而残害老百姓的鬼子、国民党,老百姓当然支持我们。于是,老百姓的眼睛成了我们的眼睛,老百姓的耳朵成了我们的耳朵。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敌人是瞎子、聋子,能不败吗?
老百姓拼着性命支持我们掩护我们,多少战友视死如归,无数悲壮惨烈的往事像溅着火花的烙铁,在我的头脑里烙上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不能想钱,想钱的都是汉奸王八蛋!
我第一次听到“股份公司”、“股票”这些词,是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老总(陈毅)在丹阳给我们即将进入上海的同志做报告。他批评一个同志,以1941年入伍为理由,写报告给上级,抱怨给他的职务太低(当时接收上海有军代表和联络员两级职务,他是联络员)。陈老总激愤地说:“共产党不是股份公司,你1941年的‘股票’算啥子!井冈山的骡子现在还驮炮呢!”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股份公司”、“股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抱怨职务低”本来是件小事,遭陈老总如此斥责,是因为他“撞在枪口上”了。陈老总是传达刚开过不久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决议“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而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地方,最容易感染享乐思想,据说李自成、洪秀全都是这么失败的。二中全会特别强调要防止党内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情绪的滋长;以资格老为理由抱怨职务低,就成了以功臣自居的典型!
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其实就是要我们继续保持不爱钱的观念,因为爱钱就是为了享受。陈老总列举了上海滩纸醉金迷的腐朽享乐生活之后说:“上海有七百万人口,而我们进入上海的同志与之相比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我们是处在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究竟是我们改造上海,还是被上海的资产阶级改造,同志们可要警惕呀!”所以,在进入上海之前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我们不爱钱的思想来改造上海资产阶级爱钱、讲钱的观念”。
用“不爱钱”的思想改造大上海
说也奇怪,当我们这些土包子涌进城后,上海发生了巨变:地痞流氓、贩毒吸毒、卖淫嫖娼、抢劫盗窃等等一切坏人坏事,都闻风丧胆,消失殆尽;连历届政府都怕他三分的帮会头子黄金荣,也吓得忙不迭地认罪,拿着扫把扫街,以示他要弃恶从善。
他们之所以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想钱,从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钱。(当时)政府部门包括改称公安局的原警察局以及国营大企业的领导人,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土包子。上海周边的县,也是由我的家乡——胶东老根据地搭配的领导班子,如奉贤县的领导干部是来自蓬莱县,青浦是来自黄县,昆山来自海阳县……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土得掉渣,但不爱钱,不想钱,不要钱。
一个在火车站控制三百多个小偷的帮会头子,被捕后告诉我(那时我是铁路公安,见下图),他和国民党的警察“都是好朋友”,意思是也要和我交朋友。他拍着胸脯说:“你把兄弟我(其实他年龄比我大一倍)放了,钞票、金条尽你要,今后你们在火车站丢了东西找我!”他的话使我明白:国民党警察爱钱,所以官匪勾结,难怪小偷横行肆无忌惮!
我们的“不想钱”和三年前从鬼子手里接收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大量搜刮形成了鲜明对照。上海人民因而对我们十分好感,使我们耳聪目明,坏人坏事无处遁形。50年代的上海,居民夏天怕热,开着门睡觉,真个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更使我相信:不想钱的思想不仅能打败敌人,也能治理好大上海。
可现在竟有人说,我们这些土八路进了上海都被资产阶级生活所征服,如香港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传奇》(作者施为鉴),该书41页有这么一段话:“事实上,从北方农村(主要来自山东)进了上海的共产党干部,无不被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奢靡所征服”。
撇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告诫不谈,其实来自穷乡僻壤的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上海的繁华和奢靡。我们向往的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的享受莫过于“吃饺子”,以为“蒋介石天天吃饺子”。对上海人的打扮也看不顺眼,还编了顺口溜嘲讽穿短袖衫长丝袜、烫发抹口红的妇女:“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绵羊尾巴猴屁股嘴”。对上海的的繁华和奢靡我们不是羡慕,而是反感甚至敌视,认为“这是剥削阶级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一定要改造”。
虽说我们不是决策的高干,但能摇旗呐喊,影响决策。也许决策的高干也和我们想法差不离吧,这不,上级出台的决策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如当时提出“要把消费的上海改造成生产的上海”,于是,“跑马厅”成了“人民广场”,“逸园跑狗场”成了“文化广场”,夜总会、舞厅之类或改头换面或销声匿迹;股票、证券大楼的取消,还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认为那是“破获了一个洋式赌博大集团”。更重要的改造是:把资本家的工厂、商店全归公,把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社会风尚大变,人们五彩缤纷的穿着,变成“蓝色的海洋”;秧歌舞、腰鼓舞取代了交际舞;软绵绵的流行歌曲也被激昂粗犷的《翻身道情》、《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所取代。人们的观念不同了:穷人光荣,苦大仇深最好,富人都是吸血鬼……在我看来,“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终于改造了上海,而没有被上海所改造。
“改革”就是改变我们那“不爱钱”的观念
如此造成的后果是:奢靡没有了,繁华也日渐衰落。但我们认为,这才是“生产的上海”、“劳动人民的上海”。我们的“不爱钱”的观念必将创造更大奇迹——生产将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人民将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然而,后来的事实却相反:别说英国美国,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香港、台湾同胞,人均产值竟是我们的十几倍,冰箱、空调、电视、洗衣机……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而我们呢,家里有个“红灯”收音机就算不错了。
何止是物质匮乏,精神方面也很糟——因为“不爱钱、不讲钱”,所以“不能用物质利益腐蚀劳动人民”,只能讲政治思想、讲阶级斗争。于是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不知折腾了多少好人,毁坏了多少文化,造成了多少悲剧。“革命”搞得人人自危,连我自已也成了反革命、走资派,关进了牛棚……“不爱钱”的思想之花竟结出如此恶果,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改变我们那“不爱钱”的观念,明确提出“要坚持物质利益的原则,不搞政治挂帅”。深圳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位经济学家更直言不讳地说:“钱是社会里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为社会多作贡献,不应回避钱,把它看成坏东西”。所谓“改革”,实际就是把我们当初在“不爱钱”的观念主导下改造掉的一切“恢复”过来。比如:“恢复”了市场经济,资本家又以民营企业家的名义出现了,股份公司、股票、夜总会、舞厅应有尽有,赛马、赛狗虽未恢复,但有了彩票、赛车……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后,上海简直像脱缰之马向繁华疾驰。几十年来作为上海标志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早已淹没在成百上千的更高的楼群之中,天上的轻轨、高架、越江大桥,地下的地铁、过江隧道,拓宽的马路和冒出来的数不胜数的公司、大卖场……弄得我这老上海出门不认路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的变化,虽说穷富差别大了,但总体说来是好到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步——不仅衣食无忧,电话、电脑、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几乎家家都有,拥有私家轿车甚至几套住房的也是稀松平常。
我奇怪:我们不爱钱,刻苦自已,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什么却给人民带来困难甚至灾难?我们不追求享受,提倡艰苦奋斗,“高积累、高投入、低消费”,为了多产粮,提出“以粮为纲”,连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风景点也除去花草种上庄稼,可粮食却总是不够吃,不得不定量分配凭票供应。而现在,绿化和建筑占用了那么多耕地,许多地方还“退耕还林(湖)”,耕地面积锐减;且举国上下吃喝成风,什么“生猛海鲜”、“四川火锅”、“澳洲鲍鱼”、“美国龙虾”……大吃特吃,粮食反而越吃越多,食品越来越丰富?
未能实现的关于“平等”的乌托邦
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使我有所感悟:各式各样的商品任你取用,不用票证,只要钱;你只须发挥你的特长和聪明才智,做出并提供人们需要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市场取得钱,就能买到你所需的一切商品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表明“钱”在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上的巨大作用。而我们的“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特别是束缚了上海人的聪明才智。比如,东方明珠电视塔,本是为电视发射由政府埋单的建筑物,却搞成旅游风景点,使上百亿的钞票滚滚而来。我真佩服上海人的聪明才智(至今只有上海这么搞)。
我又想,事情的发展恐怕也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革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的,自然把我们这些土包子推上了城市的领导岗位。而敲石取火的经历,使我们易于接受“商品经济是唯利是图,是掩盖资本家的剥削,是要把牛奶鸡蛋倒进海里……”,却难以理解商品经济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让人们过上物质、精神产品都极大丰富的现代化生活。
我愧疚、委屈,又有失落感,因为我原以为我们“不爱钱”的思想可以建立一个世界上最美好、最公平并真正平等的制度——不仅政治上平等,更要经济上平等——经济上不平等,政治上不会真正平等——工人能和掌控他“饭碗”的老板讲平等?所以解放后我们消灭了资本家这一社会阶层,宣布“工人有劳动的权利”,不再有失业,看病不要钱,并一再缩短工资的差距,当时许多工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但二十多年的事实说明,这制度虽说公平却未能促进生产,倒成了养懒汉的“大锅饭、铁饭碗”。更令我困惑的是,农村消灭了地主之后,生产力明显发展,而城市消灭了资本家却使生产倒退。结果是三十年后又出现了大款、老板和打工仔、打工妹之分——人和人的真正平等还能不能实现?
钱,是人们喜爱的(也理应喜爱),但人们并不喜欢“特别喜爱钱”的人。所以,“不愿招惹人们的反感”成了我至今仍然“不爱钱”的理由。
(作者系铁路局离休人员)
敌人之所以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想钱,从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钱。(当时)政府部门及国营大企业的领导人,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土包子。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土得掉渣,但不爱钱,不想钱,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