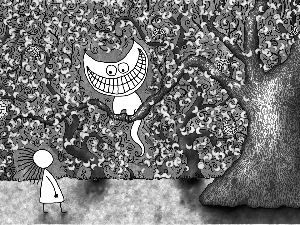|
⊙【读品】出品人 李华芳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趋缓,“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崛起让新儒家也趁势而起。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中很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华人家族企业就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提供了动力。而这些家族企业以前一直在企业研究的视野之外,它们的制度与行为和主流的“新教伦理”下的“现代企业”格格不入。但就是这些家族企业成了解释亚洲奇迹的重要因素。
哈佛大学的怀默霆在《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论述中国的家庭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阻力还是动力问题。怀默霆曾经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潜心研究中国家庭很多年。他观察到,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中的“忠诚和信任”可能会模糊家庭资源的产权,会导致没效率或者效率很低下;但同样是这种对家族成员的“忠诚和信任”也可能使得成员为家庭尽心尽力,这也恰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所谓的“关系”、“模糊产权”等因素何以能推动经济的增长。
后来,黄绍伦将此类家庭成员概括为“家族主义企业家”,按照通俗的说法,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儒商”。黄绍伦延续了熊彼特对“企业家”和“创新”的论述,认为即便是在“家族主义”传统下,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没有被抹杀,不过是不同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影响下的企业家行为而已。而杜维明则进一步阐释了儒家传统对华人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影响。
尽管欧美现代企业制度风行一时,但传统的家族企业始终存在着,生命力强盛,这使“产权清晰论”遭遇了不小的困境。储小平在《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中,把家族企业的这种模糊产权和柔性管理等等都看作是企业家调动社会资本的方式,如此一来,家族企业就能借助“泛家族关系”利用资源,进而扩展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但问题在于上述论述都只说明了家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其第一代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而现在华人家族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维系家族企业的经营,或者说如何打破传统的“富不过三代”的诅咒。李秀娟和李虹这本《富过三代:破解家族企业的传统诅咒》,就试图给出解答。因为假如家族企业不到三代就垮了,那么长期来看,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要大打折扣,进而“家族主义企业家”的说法也不一定能站住脚。
正如李秀娟在书中提到的那样,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这一背景下正蓬勃发展,人们在对它们充满期待的同时也不免担忧:现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能否成功摆脱“富不过三代”的传统诅咒?这一问题也构成了《富过三代》一书的起点。李秀娟以个案切入细节,从微观上解释了家族企业的经营、传承、如何化解内部矛盾、如何完善治理结构以及如何选择战略规划等五个方面,也从这五方面来回应宏观上家族企业如果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本书的个案剖析如同陈凌等的《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一样,在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家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画像的同时,也试图为它们立碑。
李秀娟在这本《富过三代》中实际上是将五个方面归结为所谓的“家族企业接班人”问题。例如今年跃升《福布斯》富豪榜首位的碧桂园的杨惠妍由于其父亲给予的股份,一举成为首富。这是一种交接方式。但李秀娟也通过世界各地家族企业的特色分析表明,并不是只有家族化管理这样一条阳关道,在家族企业管理上也可以走职业化道路。当然欧美的保时捷和福特等家族企业与亚洲的家族企业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李秀娟也回溯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历史,认为家族企业实际上要处理好“企业经营、所有权和家庭”这三极的关系。“三极发展模式”最早由盖尔西克在《家族企业的繁衍》中提出。但李秀娟通过希望集团和万向集团的研究表明,中国家族企业在处理三极关系上尚有许多问题,因此是“有待完善”的。
实际上,家族企业的永续经营问题与现代企业之间也有诸多联系和共通性。除了家族企业特有的“家庭”这一极外,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企业都需要面对“基业如何长青”的问题。《富过三代》最后将“基业长青”的源泉归于“创新”,是很有道理的。这不仅意味着企业家本身的创新精神,也意味着企业制度本身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