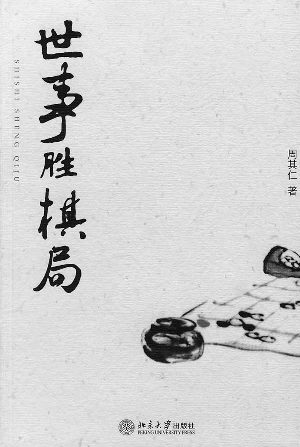|
睿智的威柏有一句书评讲得甚是精彩:“没有读两遍价值的书,就一遍也不值得看。”好书好文章确实值得读两遍或两遍之上。周其仁先生是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他结集出版经济学随笔集子,我以为是值得读两遍或两遍以上的,所以总是很留心。比如这本《世事胜棋局》。
一如先前的众多文章,周先生为文最突出特点是从经济生活的细节入手,通过对细节的抽丝剥茧,廓清迷雾,找到常识,进而得出理性的合乎经济逻辑的结论。如他在“对国际话费的感受”一文中说:“我绝不谴责国内电信公司贪图暴利。相反,我质疑他们为什么没有赚到更多的钱?读一下中国通信业统计年报就可以知道了。2005年中国固定电话本地网内区间通话量827.4亿次,区内通话量6211.9亿次,固定传统国内长途时长894.1亿分钟,可是国际去话通话时长(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只有11.6亿分钟。移动电话本地通话时长11788.6亿分钟,国内长途通话时长713.5亿分钟,国际通话时长(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不过区区6.6亿分钟。什么叫‘去话通话时间’?就是国人打出去的电话。至于从国际上——包括现在全世界无处不见的中国人——打到中国的通话时间,应该有20倍还不止吧?后果很清楚,大生意被别人抢走啦。”
这段文章所描述的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见到。比如我的好友老李,他说这几年他与在澳大利亚就学的儿子通电话,几乎都是他儿子先拨,他在国内等接,即使有时候偶然他先拨,也是打通后,立马挂断,等他儿子再打过来。这样做当然只有一个目的:节省话费。他们是节省了话费,可利润也让外国的电信商赚去了。周先生谈论这个话题,高明之处在于他通过对两个看似很小的数据的比较,即“去话通话时间”和“来话通话时间”,得出“大生意被别人抢去啦”的结论,这个结论与“薄利多销”的商业常识是相符合的。能在海量信息数据中发现关键的信息数据,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这正是周其仁先生的厉害。
对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不少人偏倚极端,常常自以为非此即彼,对错分明,这显然是幼稚的。周先生虽被不知所谓之辈封为“原教旨市场化分子”或“市场崇拜者”,但他并不反对政府管市场的事。他在《9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盖多高?》中说:“政府还是要管。不是应该不应该管,而是情势所迫,非管不可。”只是,他也明确提出:“政府在处理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经济问题时,要为利用和发挥经济规律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黑板上或许有,真实世界绝对无。这一点没问题。”“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经济问题”,在下的理解就是指“市场的外部性”,这是需要政府伸出“有形之手”予以合作的。
周先生时时不忘“真实世界”,处处不忘“市场智慧”,当然是有深刻背景的。Josiah Ober在所著《在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一书中,以雅典的民主政治为案例,讨论多数人的智慧为什么高于少数精英的智慧的问题。Josiah Ober认为,大众对许多问题虽然无知,但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在各派精英和专家的意见中作明智的选择。精英们想要在城邦政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当然这是历史的结论,现实则要复杂得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不论精英还是大众,其实都是有利益、有立场、有血肉、有情感、有情绪、有思想且理性有限的自然人,都有可能出现错误,所以周先生才强调,需要政府干预,但同时也需要大众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我想,这正是周先生胜过那些个偏执一端、不及其余的非此即彼者的地方。
有人说,智慧的极至境界是幽默,读周其仁先生文章,不难领悟到,此话确是至理。中国古代文论有“篇句之辩”,讲文章全篇与单句的关系。作为经济散文,周其仁先生的落笔从整体全篇来说,是“正说”,而从局部单句来说,则不乏“趣说”。读他的随笔,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看见他给你幽上一默,而且他的幽默往往能叫人拍案叫绝。你看“限高政策管用呼?”的最后一句:“行政机构和官员决定调控政策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落下了”,熟悉周其仁文章的读者读到这里当会会意一笑,这分明是“幽”那些在做政治决策时把自己“置之度外”的官员的“默”。官僚系统里的某些人是贼不空走雁过拔毛经手肥,连大学师生捐给灾民的衣物也搂,所以在“何处用心?何处用脑?”一文中,周先生冷不丁来了句:“以后捐助衣物的时候,大家就多了一番心思:究竟哪些东西是那些权力分子不要的呀?”在谈论严肃话题时,突然插上来一句俏皮话,这正是周先生举重若轻的表现。此文最后一段其幽默更是精彩之极:“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自然科学家,他们少有这样的困扰。推断地震的发生条件,一般不会被人怀疑‘喜欢地震’;正如研究艾滋病,通常不会被怀疑‘究竟拿了艾滋病多少好处’。研究人在社会里的行为,麻烦从来就比较大。用脑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要经过情感甚至情绪的蹂躏和审判。不问青红皂白的‘愤青’倒也罢了,可是居然还有‘愤老’。有什么办法呢?慢慢来吧。”
《世事胜棋局》
周其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