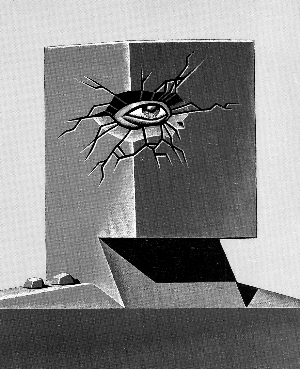|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这些天来围绕诸如捐款管理、大灾预测与应急、倒塌楼房质量、80后的团体精神等问题的思考与争论,让我们回味良久。是的,面对大灾,善良的心和勇敢的行为的确应值得褒奖,但理智的反思和前瞻性的思索更需要提倡。
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泉之一。这里的氏族社会不指代什么具体社会阶段,而是体现为家族制、宗祠制的社会形态。此时,人们不仅受到同样文化的精神洗礼,而且在困难时也会有相互帮扶的事实。因此,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虽然近年来这种精神遭到了金钱至上观念的强烈冲击,但要将其彻底从中国人心中完全移除出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不是技术,难以复制,总是与特定地理空间之上的生命体相联系。汶川地震之后所显示出的同胞相助之情,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也会呈现出新的继承性变化。面对地震之后的钱款捐助管理问题,许多人纷纷要求应由与政府无关的独立社会机构依法管理捐助的钱款。西方国家目前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效率很高。这样的观念认定,由政府管理捐助款很不合理。一方面,不免将之与政府财政相混淆,以致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混淆,另一方面,面对捐款,很难说就不会产生贪污腐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历史根源。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在历史上是信托型的,即相信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做好事情。而且,这种管理模式是政府与民众共同认可的,至少在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比较成熟,基于社会监督的契约性管理模式就成为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必然选择。
在历史文化绵延传递过程中,中国这种政府信托式的捐款管理模式继承了下来,在社会缺位的前提下,这种管理模式也没有被打破的动力,这便造成了西方国家与我们的分歧。其实,不同的捐款管理模式在实质上本无差异,都是为了更好帮扶弱势群体。但效率的差异,却是与外在的因素密切相关,如外在的监督、法制的约束等等。显然,当前我们要做的是并不是匆忙地构建一个非独立运作的、有利益诉求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要循序渐进地改革。一方面加强账目管理的透明性,并对其进行专业审查与监督,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机构的独立与完善,直到一个健全的、独立的社会体系形成之后再实施全面的社会化管理。
此外,在震后的话题中,对于公众人物捐款数额的讨论也是非常多的。不少人在网络上对一些名人的捐款品头论足,有极端者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笔者无意责备这些评论,因为他们也是出于对灾情的关心,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有能力人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正如,有人曾经援引电影《蜘蛛侠》中的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来为自己的言语证明。殊不知,能力大小并不能与金钱多少相挂钩。“莫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告诉我们,切不可攻击善小者。古人云,孝者,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同样,在从事善举时,不应以金钱多少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别人的善举,要报以感恩的心态。试想,为抗震救灾,“一人有难,八方救援”的善举正塑造着一种良好社会风气,而攻击和评议却又掀起一种社会暴戾之气。这是多大的讽刺!
在人们竞相捐款的过程中,许多单位张贴了光荣榜,这个小小的榜在某些时候成为引发争议的大事情。笔者曾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家医院里,一位护士在第一时间里以无记名的方式向捐款箱里投了五千元,事后在反复查证下,这位护士的善举终于被单位同事所知。但是,在第二次捐款时,这位护士却只捐了100元。其实,前后的反差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这位护士从热烈到冷漠的态度转变,而是因为捐助原本就是善的表现,当善不为人所知时,行善体现的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祝福和对他人的真切关切,一旦善举成了别人的聚焦点甚至被拿来攀比,则这善举早已大大蜕化变了味!
同样的情形,又有人拿中国人和外国人做比较,仅仅因为外国人的捐赠通常普遍要比中国人多,便认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精神和善良品行。事实上,这种理解大有问题。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代际传授,一是性善论。中国人家族观念很强,非常重视代际间的传与授,捐赠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比如,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在这里,“经”是获取黄金的途径,比黄金重要,因此需要传给子孙。而西方人通常更重视个人主义,特别强调公私之别,故捐赠动机大于传授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孔孟之道是以性善论为基点,这种善就是与人为善,在必要的时候,捐助又会不断发生。而西方文化传统是以性恶论为基点,因之捐助、赠与便成了赎罪的主要手段,西人捐赠之风遂大规模形成。
震后这一连串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争议问题,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好好吸取的教训。在着力推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培育的当下,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更需要立足未来,不要总是在事发后才去规避不良的态势,这样只能伤害更多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