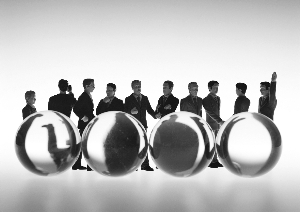|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如果我们能调整经济增长路径和生活方式追求目标,在发展中国家率先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和生活方式追求道路,才算真正做到了及时自省,也才更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政治协调中,会同主要经济体建立起一个新型全球协调机制,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具质量。
“世界已经慢慢认识到我们今年正生活在现代历史上一次较为严重的经济空难的阴影中,在此时节,衰退可能由于心理因素而发展得有些过头。”这是凯恩斯在《1930年大萧条》中对当时形势的界定。78年后,凯恩斯曾参与筹划的国际清算银行发表最新年度报告,对2008年经济金融形势下结论说:“当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发生的市场动荡,在战后时期是没有先例的。”言外之意,类似先例只能到“战前时期”去找。眼下是否存在凯恩斯上述“战前”1930年那种“严重的经济空难的阴影”呢?对此,经济学者的争论肯定很激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当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市场下跌时,在经济学者的圈子里,悲观的总比乐观的多,并且普遍比一般人更悲观。经济繁荣时,经济学者的乐观预期往往比普通人还激进。
当前,大多数人恐怕还没有来得及从过去多年低通胀、高增长、金融市场快速聚财的兴奋留恋中摆脱出来,就一头雾水似地震惊于信贷市场大幅收紧、资产市场超速缩水、金融机构破产、石油与粮食价格打着滚儿上涨等一连串的坏消息中,通胀成为全球“明显而迫近的威胁” 。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争吵开始升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说:“你们不能像我们这样生活” ,并指责后者推动了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以及环境问题;低收入国家则埋怨高收入国家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的信贷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加节制地消费。致使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争吵声中,世人再一次切实感受到:经济是全球化的,而政治仅仅是国家层面的。
但问题是,对尚处于货币文化时代的人类而言,政治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竞争,政治分歧将少得多。因而,经济的全球化,最终无法摆脱政治协调机制的全球化。如果迟迟建立不起一个有效的全球政治协调机制,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各国经济增长都将受阻。当个别强势国家难以忍受这种“阻碍”时,战争将成为他们选择的、也是最坏的调整机制。为了避免这种最具破坏性的调整,全球各个经济体应当学会妥协与合作。这恐怕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协调机制所赖以建立的理念。
任何妥协与合作,都意味着自省。这是起码的前提。我们不妨以眼下讨论的焦点——通胀为例来说明。作为经济增长最快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不能从“输入型通胀”的意识中走出来,将很难真正自省本身的经济问题,也就很难有效地参与国际政治协调。
相当一部分舆论认为,国内通胀抬头是由于国际石油、粮食、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对国内市场输入造成的。尽管人们可以指责金融投机对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推波助澜,但应当清醒的是,金融投机从来就不是通胀恶化的真正元凶。因为,投机向来是冲着问题而来的。如果某一领域里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非均衡问题,那些异常聪明而追求时效的金融投机资金决不会在这一领域里浪费精力和时间。所以,价格升降的最根本力量是供求,而需求又无法不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次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中国因素”是显著的。
且不说,中国已经成为包括铁矿石等很多原材料的第一大进口国,占了2007年全球新增石油消费的36%,仅就全球工业化布局的重大变化看,工业化过去仅仅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能源原材料主要由他们大规模消费,随着其工业化的成熟,他们的消耗水平也趋稳定;而现今,拥有近24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过去10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化速度加快。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工业,而印度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服务业。支撑工业化的化石燃料和原材料消耗水平的新需求成几倍地迅猛增长,在过去十多年全球能源原材料供给能力投资并没有大幅改善甚至稍显停滞的情况下,如何不成为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成倍翻番的根本力量?!占新增需求相当部分的中国经济,又怎么不是其中无法忽视的主要因素呢?!
当然,凡是追赶者,总觉得自己的速度不够快。然而,那种不计成本的速度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难以持续的。仅就私人轿车拥有量而言,中国即使达到本世纪初欧洲每5人一辆的水平,就意味着家轿拥有量将从2007年底的1522万辆(每80—90人拥有一辆)膨胀到3亿辆,平均每年增加近1400万辆,仅此一项,就不知将会带动石油需求增加多少。更不用说,若达到目前美国每两人拥有一辆的水平了。除此之外,尽管服务业已成为印度的骄傲,但不同于那些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这只能说明印度工业化的落后及其空间的巨大,迟早将返回来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印度已在开始行动,其目标首先是在制造业上赶超中国。这意味着,印度的能源原材料消耗增长将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所以,如果中国不调整经济增长路径和生活方式追求目标,无法在发展中国家率先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和生活方式追求道路,那么,真不知届时能源将紧张到何种程度,价格飞涨到何种水平。而这反过来,又将极大阻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
以此观之,伴随这次全球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未见得不是好事。况且,随着同发达国家技术前沿距离的缩短,以及经济基数的增大,增长放缓也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应当利用这次增长放缓之际,让某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在增加压力的同时,也使政府和微观实体,能够正确检视宏观政策和微观运营策略的得失。特别是,在减轻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压力的同时,理顺国内价格体系,减少行政控制,降低各方面的通胀预期,更冷却国际金融投机资金针对“中国因素”的热情。最为根本的,应当是在总量增长放缓的压力下,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唯有如此,我们才算真正做到了及时自省,也才更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政治协调中,会同主要经济体建立起一个新型全球协调机制,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从而使中国增长更具质量。当然,如此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高收入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