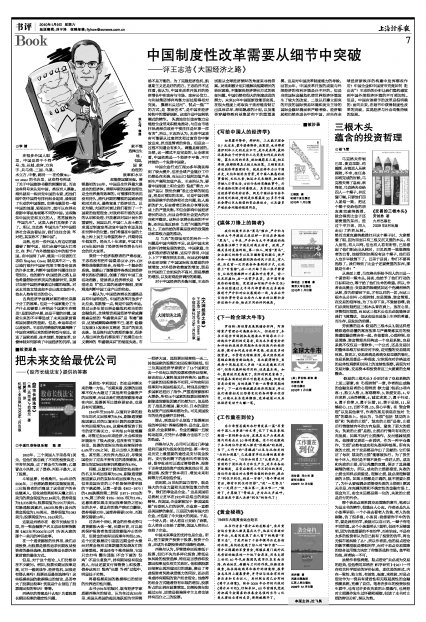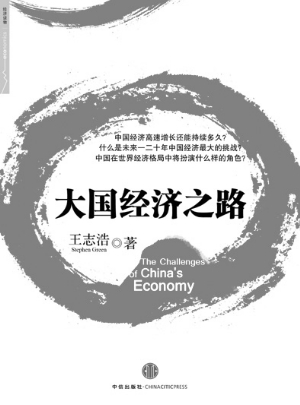|
⊙李 婧
在很多外国人眼里,中国是若干个符号:龙、长城、故宫、方块字、兵马俑、三国、鸟巢、水立方、中餐,姚明……在伦敦Water stone 的书店里,这些符号构成了关于中国旅游书籍的斑斓封面。而由这些符号来认知中国,类似盲人摸象。海外就有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把他们眼中的中国符号排列组合起来,绘制成了生动的中国图画。如果电脑里有一幅中国的地图,轻轻回车,就可以在浮光掠影中零星地领略不同的中国。这些熟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常常被称为“中国先生”。这类人我们见得多了去了。所以,当此类“中国先生”对中国经济社会表达看法时,我们往往会说“不对吧,其实你不了解中国”。
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有迫切的愿望要了解中国,他们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在“庐山”内外描绘变化中的细节中国。在中国待了6年,能说一口汉语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就是其中之一。他以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身份发表的许多文章,判断中国经济问题往往非常到位。他的新作《大国经济之路》,是他希望借助世界顶尖的最新研究,来探讨当前中国经济最紧迫问题的结集。对这本用英文写成却不会出英文版的书,他本人抱有相当的信心。
古典经济学强调财富的增长来源于分工的效率。但是一个国家能分工生产什么却要看上帝把这个国家生在哪里?是肥沃的平原,还是干涸的沙漠。国家生来的不平等造成了未来国家贫富和国民福利的差距。但是,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王志浩用精炼的笔墨阐释了中国自宋朝以来的经济转型与变迁。论述了国家治理、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官僚体制如何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沉浮。国家不能选择出生地,但是,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却能使国富民强。清朝最初的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可惜那样的状况没有持久,清代后期的糟糕的国家治理和闭关自大,最终窒息了经济活力。以史为镜,大国的兴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理念、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开放意识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民国以后,中国仁人志士都力求通过制度变革改变中国的命运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种上民主与希望的种子,并期待其生根发芽。经历几十年求索,中国才自1978年起开始了经济的神奇增长与社会的巨大变革。
秉持一个经济观察者的严肃态度,王志浩没有把中国看成GDP、PPI、CPI等经典指数的组合,而视作一个复杂的系统。他提出了谨慎看待各类反映经济增长指标的建议,创建了渣打中国工业活动指数,使读者从经济增长是“W” 型还是“V”型之类的迷惑中解脱,更客观地判断中国工业产出的状态。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子比拉美、东欧慢一点,倒是中国的幸运。经过10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金融危机,全球指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总结的“华盛顿共识”是“有毒”建议,这使威廉姆森痛惜不已,遂在《金融与发展》上发表长文阐述“共识”的来龙去脉。但是流行成为真理的象征,很多人指出两次危机都说明了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失败。市场不是万能的,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还是好的药方。王志浩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中在政府与市场、政府公信力、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方面处理得相对完美。“摸着石头过河”、“试点—推广”的方式,是“政治艺术”,是中国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创新。这或许是中国转轨模式的精华。“天真地信任政府能力总能给企业带来积极地推动,与自由市场狂热者深信政府干预往往是坏事一样有害”,所以,王志浩认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要从过度担忧和过度自信中解放出来,担当监管者的角色。但是这一过程不知道会有多久。调整是痛苦的。当然,这一模式不是完美的,从全球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企业行走江湖30多年确实得到了较大提升,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然处在末端,而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王志浩认为,要看中国制度上和企业的“追赶”潜力,中国产品以“质优价廉”胜出全球的制造业,将是可预知的未来。可是中国仍然面临更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标志着老百姓在分享增长收益上的严重失衡,不但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会带来社会更大的冲突和不稳定。这种分享增长收益的不平衡,还突出地反映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上。王志浩给的答案是政府的政策推动和草根力量的推动。
与“三农”的烦恼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内需的不足,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软肋。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储蓄,这似乎表明,中国上上下下都在担忧未来。而且这种储蓄状态还导致了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加,对外经济依赖度的增加,贸易伙伴国的工会组织的不高兴,贸易摩擦的增加,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难题。
对于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王志浩试图从全球经济循环的角度来寻找答案。财政刺激计划只能解决短期增长的临时困难,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制度改进的潜力。未来10年中国版新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府能否制订出具体详尽、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及能否穿越特殊利益集团布下的重重迷雾。这是对中国改革制度能力的考验。回首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外部经济的有利环境是分不开的。但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和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严峻考验。经济崛起和仍然在成长中的中国,应当在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哪些作用?中国企业和中国货币究竟如何“走出去”?王志浩的分析让我们隐约感觉到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可预知性。但是,中国应该着手的改革是很明确的:面向未来,在细节中获得制度性改革的突破,实现经济与社会均衡持续的发展。
《大国经济之路》
王志浩(Stephen Green)著
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