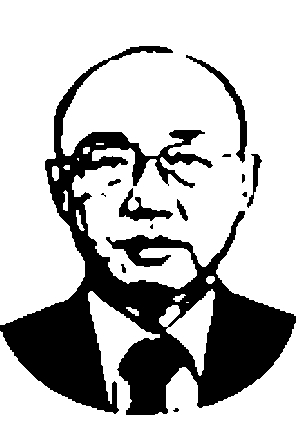|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拒绝向希腊提供贷款,本来只需要花几百亿欧元就可能化解的一场危机,现在却需要欧盟和IMF联手出资7500亿欧元,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当然,正是由于希腊政府长期寅吃卯粮,还向欧盟和欧洲央行隐瞒本国实际的财政状况,才酿成如此严重的危机,并拖累欧元区和世界经济。但是,不管默克尔政府如何辩解,德国最初对希腊危机袖手旁观,在客观上对这场危机的愈演愈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1年12月,欧共体决定将发行单一货币——欧元时,不少专家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这么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传统的经济政策迥然的国家使用同样的货币和采取同样的货币政策,同时各成员国还继续制定和实行各自的财政政策,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些专家没有看到欧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货币:欧元的基础不是经济,而是法德之间的战略共识和合作。欧洲一体化的初衷就是要解决战后的德国问题,其思路是通过一体化把实力最强的德国牢牢地拴在西欧大家庭内,以实现“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目标。1990年前后,面对德国重新统一的趋势不可阻挡,德法两国领导人谋划了德国和欧洲的前途。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说法,密特朗最后对科尔说:“你给我一个马克,我给你一个国家。”密特朗的意思是:如果德国同意放弃作为战后德国经济复兴象征的马克,使德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融入欧洲,法国就同意把东德“交给”西德,让两德统一。毫无疑问,这笔交易在经济上对德国是有利的。因为,虽然欧共体建立了所谓的“共同市场”,但是各成员国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保护本国的市场(例如,通过调整汇率来影响进出口贸易);仅仅因不同货币的兑换和汇率波动的风险,就使“共同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提高3%至5%。一旦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德国就能更加通行无阻地将其商品行销欧洲各国。因此,密特朗在向法国民众解释时说,只有把“浴缸”做大,才能容得下“大胖子”,即统一的德国;否则,在欧洲大家庭内感觉不舒服的德国又要“自行其是”了。
当然,密特朗也不是“傻瓜”。 对于“有历史问题的”德国来说,以雄厚财力为欧洲一体化“埋单”,是一种“救赎”行为。密特朗上述让步的“潜台词”是:得到莫大经济利益的德国必须像以前那样为维持欧元而“埋单”。这对于有历史责任和战略眼光的科尔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德国历来奉行“贸易立国”的政策。如今,出口占德国GDP的40%。欧元,让德国的出口更有如虎添翼的效果。2009年,欧盟吸纳了德国出口的52%,其中81%是出口到欧元区去的。当年,德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1080亿欧元,对欧元区的顺差为770亿欧元;德国贸易顺差总额是1359亿欧元。从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来看,欧元的流通对德国也是极其有利的。1995年德国出口商品来自国外市场的附加值的比重是31﹒1%,欧元诞生的第二年(2000年)是40﹒1%,2006年上升到44﹒8%。可见,从通行欧元中得到巨大利益(包括巨额贸易顺差)的德国,在希腊危机刚开始时拿出数百亿欧元,不是勉为其难的事情。更何况,德国如果当时救助希腊的话,所提供的不是无偿援助,而是年率高达5%的贷款。实际上,德国以前为欧洲一体化“埋单”,也并非“打水漂”。德国前外长菲舍尔就说,战后德国历届政府利用本国的财政实力来推进欧洲一体化,即为欧洲“埋单”,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德国在施惠的同时从中得到利益。然而,现在的默克尔政府连这样的事情也不愿意做了。
法国《世界报》点穿了默克尔政府拒绝援助希腊的如意算盘:伯林希望趁机把希腊等弱势经济体从欧元区开除出去,这样,欧元更可能是一种强势货币。默克尔政府由此可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双丰收”。因为,在政治上,把欧元变成“新马克”的默克尔政府可获得对马克有“恋旧情结”的德国民众的支持;在经济上,对于依赖出口的德国,特别是已经把许多在本国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去和在这些市场大量购买零部件的德国企业来说,强势的欧元有助于它们廉价地从欧元区以外的市场进口零部件,组装后向欧元区出口,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为此,德国前外长菲舍尔最近撰文抨击默克尔是“短视的政客”,直指法德协调是欧元区稳定的基础,喟叹“目前处于危机时期的欧洲所需要的正是科尔这样了不起的领袖”!身为左翼的绿党前领导人的菲舍尔高度赞扬政治立场偏右的基民盟前领导人,这在战后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是极其罕见的。
对于希腊危机所反映出德国追逐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安危的倾向,欧洲某些有识之士已感到忐忑不安了。欧洲外交政策学会的乌尔里克·古埃罗说,德国人故态复萌,所作所为又像民族主义者了。对于迄今仍对二战历史有切肤之痛的欧洲人来说,“德国人故态复萌”的含义,能不让他们头痛么?
(作者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