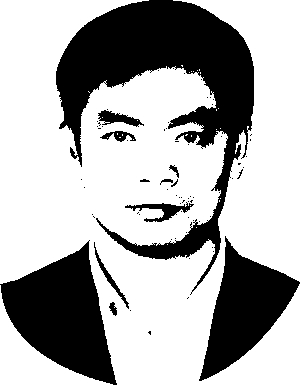|
备受国际关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边际成效似有逐轮递减之势。
从两国签署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来看,尽管彼此对各自关切的话题有所关注,体现了中美相互承认各自在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与使命,但由于双方关注的问题并不匹配,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交集受到局限。中方尤为关心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对美投资遭遇的不公开不透明安全审查以及美方极为敏感的美元体系改革等问题,均未在协定中得到体现。倒是美方做足了舆论与议题设计功课,例如,美方代表不仅要求中国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还在提交中方官员的对话清单中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更加开放,敦促中国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并希望中国再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并提高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甘被晾在一边的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于对话当天向白宫发出联名信,要求量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当然,底气逐轮提升的中国也在摸清美方底线的同时,越来越注意在战略博弈中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成效之一,便是获得美方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笔者曾多次说过,二战以来,全球最懂得玩“国家战略”的只有美国。无论是昔日的超级大国前苏联还是整体经济实力不输美国的欧洲以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不是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败下阵来,就是上了美国的当,最终不得不在美国设计和主导的国际政经秩序框架下寻找自身的国家定位。而美国之所以屡试不爽,甚至在整体经济实力因金融危机冲击而走下坡路时依然能够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显然与其超前的战略设计能力以及由其主导的机制化经济与金融霸权密不可分。美国不仅拥有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超一流智库,更不乏布热津斯基、基辛格、迈克尔·波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以及尼尔·格雷厄姆等战略理论家或实践高手,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预见性和战略谋划能力往往高出别国一大截;而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精心打造的“金融高边疆”,其超强的防范能力和金融霸权惯性也绝非一场金融危机所能击倒或摧毁。
时移世易,中国在经济规模和贸易力量方面近10年来快速崛起,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使得原本相对内敛的中国被迅速推到开放世界的政经舞台的聚光灯下,逐渐适应在美国主导的现行体制下生存和发展。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还面临着要求承担更大国际义务的压力。更难回避的是,中国的崛起,正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世界政经版图,而美国作为既有国际政经秩序的设计者、主导者和既得利益者,势必对此产生不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不安心理下的逻辑衍生品。而美国也深知,以强硬姿态和中国打交道不仅收效甚微,还会损害自身利益。因此,怀着复杂对华心态的美国还是理性地选择和中国举行战略对话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重大利益问题。
尽管王岐山副总理一再告诉美国人,中美实力差距大,包括全球经济复苏在内的重大问题的求解依然要看美国,但在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家看来,经济实力与自信心不断上升的中国,肯定会寻求分享或者切割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在美中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面前,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在美中战略利益互动中,只能日益倚重其业已动摇的机制化霸权力压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以继续掌控中美博弈主导权;必要时还得由一向善于抛出新议题的学者们配合,通过描绘所谓的中美共治图景来“引诱”中国沉醉其中。
深谙趋势发展和国家竞争战略的美国,之所以愿意启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根本动因还在于借助中国恢复其曾经无可匹敌的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美国异常关注中国在美国一向傲视全球的金融领域的动作走向,也十分担心中国在包括新能源、高铁在内的实体经济领域把美国甩在身后。因此,美国必须在中国整体竞争力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依然掌控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美国握有的技术标准,“锁定”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只要下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权在美国手里,美国就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在将自身从经济与金融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若真如此,届时中国要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博得主导权,难度无疑很大。
因此,中国若要在后续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谋求主动,进而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既需要展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要在关键议题设计时,就关乎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切莫在既有国际与双边秩序框架下跟着美国脚步起舞。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