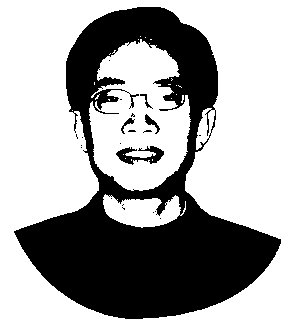|
丁骋骋
在探讨中国经济成功的诸多文献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两个广受重视的解释变量。其中,财政改革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有强大解释力的核心因素。钱颖一和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温加斯特等学者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和以财政包干制为特征的财政分权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这一论点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和验证。与财政改革不同,金融改革被视为一个令人尴尬的解释变量。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在2005年就曾提出疑问:照西方标准,中国法律制度和金融系统并不发达,但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有悖于LLSV以及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法律、金融与增长关联”的理论预测。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拉古拉迈·拉詹等人也曾指出,鉴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在国际发展经验中的因果关系,滞后的金融体系使得中国成了一个反例。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是在财政分权和金融集权的框架中取得的。由此带来的困惑是,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作为理解各国经济成功的两大维度,为何在中国的解释力如此大相径庭?笔者注意到,不少学者的研究是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视为两条平行线索,并单线条地来理解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没有从两者相互关联的视角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脉络。事实上,财政与金融密不可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之间有个双向的互动机制,这种互动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资源的配置,最终关系到宏观经济绩效。考察1962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金融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自己(金融压抑)承担着某些财政功能。此外,金融集权更成为控制财政分权负面效应的配套制度安排,并以此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因此,只有同财政分权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为何中国经济在金融改革缓慢的背景下能取得长足发展。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60多年来有过多次“放权——收权”的循环。但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考察得到的结论。梳理一下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金融改革也存在类似的周期循环,并且两者在时间上基本一致。当高度集权导致经济僵化停滞之时,中央政府就倾向于放权搞活,反之则收权整顿。这些调整大都出现在经济明显出现拐折之际,并最终改善了经济的长期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收放的互动博弈和反复调整中,中国从财政集权、金融集权体制,逐渐形成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的体制搭配。
在这种体制框架中,财政分权是被人普遍认同的提法,而金融集权则不是。所谓的“金融集权”是指,与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不同,中央政府在金融体制上维持着高度垄断和严格管制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价格管制、机构垄断和垂直管理等。金融集权与金融抑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主要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垂直管理。
在“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分权激励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另一方面为限制地方竞争的金融杠杆及其引发的经济过热,在金融体制上维持相对集权以保留调控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巧妙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体制。
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是导致中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体制性根源之一,这种体制既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目前诸多困境的原因。 说起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提法正式列入五年规划已有15年,但总体实施效果并不佳,问题一部分就在于这种经济体制上。特别是当前的财政、金融体制没有转变,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是困难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只有作出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安排,同时在财政体制上加强改革力度,真正将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通过收入、支出总量以及结构安排,影响各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才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变。也就是说,财政金融体制的转变是经济转型的前提。
具体而言,从金融角度讲,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应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在中国经济从增量改革过渡到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也应实现动员型金融向资源配置型金融的转变,而这有赖于金融机构主体的市场化、价格的市场化等一系列改革,这也是一个“金融深化”的问题。
从财政角度而言,有必要进一步规范预决算制度,整顿、厘清并按期公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状况,规范投融资行为,将地方预算外、制度外财政收入逐步纳入预算内。这些举措有助于创造地方财政通过发债融资的条件,降低对银行的显性和隐性依赖。此外,财政按照主功能区的划分,更多强调公共支出比重,降低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更新在考核中的比重是有益的步骤。(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