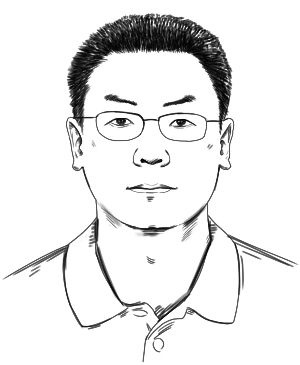|
■论道
⊙张涛 ○主持 于勇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纠结”之中: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为中国经济平稳转型增加了变数;另一方面不断积累的通胀压力,让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复苏多有羁绊。而这些羁绊之中,又以中国的货币问题最为纠结,2010年末中国的M2/GDP已经高达182%。中国是否货币严重超发?
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余额约11.6亿美元,而美国同期的M2为8.95万亿美元,日本约为9.56万亿,而相应在2008年8月底雷曼破产之前,美、日、中三国M2的余额则分别为7.79万亿美元、6.75万亿美元和6.55万亿美元,一场危机下来,中国货币供给余额接近翻了一番,已经远超美国和日本。
一般意义上讲,货币的正常供给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块,即经济增长的需要和通胀的反映,除此之外就应该算作货币的超额供给。如果连年的货币超发,同时又相应没有经济增长的吸纳,那么势必会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
2001年至2011年间,M2平均增速为18.18%,其中现价GDP平均增速为14.98%,相应十年间中国货币超额供给平均为3.2%。数据显示,3.2%的货币超额供给更多地指向了股票市场,而非是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和通胀。
而这个数据结果却和当前广被关注的房价和通胀相矛盾,如何解释呢?
笔者的理解是:伴随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的货币进程相应呈现出由商品货币化到要素货币化再到资产货币化的演变路径。
从内部而言,伴随产能供给能力的提升,中国经济逐渐告别短缺状态,相应开启了中国商品货币化进程,也就意味着超额的货币供给被不断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所吸纳;而1998年房改启动,则开启了中国资产货币化的进程,同时启动了土地的货币化进程。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正处于要素货币化和资产货币化两个阶段之间,而宏观层对房地产行业不断调控和对异化货币环境修复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造成中国货币化演变速度的放慢。
从外部而言,伴随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也把全球经济带入到一个新的货币化过程中:中国的商品输出(出口导向型),实际上就是中国商品美元化的过程,有效稀释了美国政府超发的美元。得益于美国消费和中国制造的支撑,美国乃至全球的通胀压力不大。此次危机则是把这个条件改变了,加之各国在反危机应对中投放了大量的货币,全球的货币多了起来。大量的货币跑到了大宗商品和新兴国家的资本和资产市场上。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中国城镇化进程,是中国进入市场化经济阶段最主要的两个经济逻辑。按照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结果,至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升至49.7%,而“十二五”的目标是“将城镇化率提高到51.5%”。按照本世纪头10年的平均增速测算,至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会达到56%左右,已十分接近世界60%的平均水平,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当前对于房地产泡沫担忧的加重,却在影响着这一发展。
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严重?
笔者比较了房产投资在经济中比重和中国货币化程度的配比情况,在宏观层的连续调控下,目前房产投资已经基本回到了趋势线附近,较2006年至2008年期间有了明显改善。
不仅如此,如果按照人均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情况来看,中国真实城镇化率要远低于按照常住城市人口测算出来的城镇化率,由此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二次城镇化的纠正”。
通过经过上述中国货币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两个逻辑的梳理,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纠结”,核心就是由于经济中缺乏新的增长点吸纳超发货币。
如何破解困境?对宏观策而言,承认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推进阶段还没有结束,货币环境修复要依赖于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加快,而不是单纯把货币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驱赶。(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