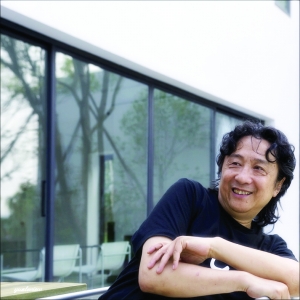自由而哀伤的灵魂
| ||
| ||
| ||
| ||
| ||
|
我把你的誓言
把爱
刻在蜡烛上
看它怎样
被泪水淹没
被心火烧完
看那最后一念
怎样灭绝
怎样被风吹散
——顾城《祭》
⊙记者 唐子韬
何多苓的画室挂着的那幅《青春》——最著名,也是他最喜爱的作品。这一幅,是原作的复制品。当年,他就是凭着这幅史诗般的作品,成为轰动全国的美术家。这是一幅有关时代与个人命运的画卷,充满了悲凉的诗意。
“诗意”是何多苓的作品的关键词。在这个爽朗的午后,在他的院子里,这个诗人气质的艺术家跟我聊起了他的艺术。“那是纪念碑,”他说,他想把那段青春,那段历史用史诗的形式塑造出来。《青春》的原作已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而今,他生活在成都郊区的荷塘边上,景色宜人,让人神清气爽。这里只有旖旎风光和清新的空气,没有历史的痕迹。
青春的纪念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成为艺术家的流行样式。何多苓是这个潮流中独特的一位。
“我的《青春》就是为了纪念我自己当知青的那段生活。也是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实践的追忆。我画的时候,考虑到不要把它画成情节性的东西,或者是生活的某一个片段。而是画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和特有历史背景的结合。”何多苓将个体的精神性从复杂的社会图卷中抽离,用一种质朴单纯的背景烘托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
一个女知青坐在山丘的一个光秃的石头上,背景是一片干枯的土地,身后一只低飞的鹰。风吹过她的脸颊,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忧伤。这就是那幅著名的《青春》。这幅画,勾起了一代人的情感回忆。
多年后,何多苓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家农场,拍摄了这片曾经洒满他青春汗水的土地。如今,农场已经荒芜废弃,这里的丘陵干涸荒凉。
“一定要把它画成一个理想的纪念碑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幅画。我打算只画这一幅,就不画了。当时有很多画知青题材的,都是一个生活场景或者某种浪漫主义的虚拟场景。而我选择了这种,有点像一个雕塑,只不过把它画出来而已,是这样一种表达方法。”
何多苓仅此一作,便完成了对青春的祭祀。
向怀斯致敬
何多苓坦言,他的早期绘画受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影响。“我当时看到杂志上对他的介绍,对他画面所表达出的意境很神往,正好符合我心中的想象。就开始模仿他画面的表现方法。”
安德鲁·怀斯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被赞誉为美国怀乡写实主义绘画大师。怀斯画中的乡村小屋、孤单的动物和朴实的人物,表现出一种孤寂感和怀乡的哀愁。在极端写实的优美自然景象和诗情洋溢的作品中,潜含着一股淡淡的的感伤。他用一种特别的蛋彩(坦培拉tempera,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画法作画,这种技法效果和画面风格带来的忧郁情调,深深地打动了何多苓。
伟大的艺术,描写的都是人类的普遍情感。当年,怀斯的画风打动过很多中国人,画中的人物游走在荒凉旷野中,身影显得弱小而孤独。这样忧伤的、富有诗意的作品深深地打动着刚刚经历过动乱年代并为之付出美好青春的人们。
“中国的所有画家都有一个母本,就是印刷品,而不是原作。因为我们是画西画的,开始大量接触西方艺术文献,从中得到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有令自己激动的偶像。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模仿他们,从中间脱胎而出。”
“1989年我去美国,在现代美术馆,看到那幅《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这是打动我的第一幅画。当初印在世界美术杂志封底。有赵一恒的一篇文章推介。那幅画我看了之后感觉非常震撼。跟印刷品不一样,跟我想象的也很不一样,画得更为单一。坦培拉的效果一看就是跟油画不同的效果。我当时只是模仿一点皮毛,但因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还是有好处的。要是真的学蛋彩画得和怀斯一模一样的话,首先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没有意义的。”
2008年,何多苓创作了一个系列作品,来重新审视曾经对自己影响很大的绘画作品。从早期的法国学院派到印象派;从美国的怀斯到英国的拉斐尔前派。这些都曾对他的艺术产生很大影响。
“我用自己的方式、现代的
方式把它们重新阐释一下,改造一下,画成我自己的画。既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因为他们在我的绘画生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是怀斯。所以我选取了第一个对我产生影响的——也就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这幅画。我完全把这幅画加以改变了。”
怀斯的画用蛋彩画法画成,光很强烈但看不到光线,分不出季节。画面凝固,光影十分尖锐,远近都很清晰。而何多苓的画则变为带着薄雾的清晨,阳光斜射,穿过画面。原画中瘫痪的女主人公在地上爬起,画面充满了压抑感。新作品则改成一个的完全脱离地面、站起来的少女身影,画中充满了明快的光线。这幅画叫《重归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代表了何多苓对艺术的重新思考和对大师怀斯的深深敬意。
文学情结
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的绘画受到文学的深刻影响。拉斐尔前派曾倡导绘画艺术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拉斐尔之前的风格,因而得名。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有着夸张的色彩和文学化的情结,作品中的那种神秘主义的气息,也曾深深吸引着何多苓。
“我的文学情结作为一种线索,始终在我的画中若隐若现。”何多苓这样概括自己的艺术。《春风已苏醒》、《奥菲利亚》、《偷走的孩子》这些作品不仅题目取自文学诗歌,画中的意境亦同样表达了文学的灵魂。
“我一直很喜欢文学,下乡的时候闲着没事,几乎阅读了所有的文学名著。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很狂热地喜欢上了诗歌,阅读了大量的作品。虽然,文学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从来不写作,从来没有尝试成为一个作家,都是凭借绘画来表达。”何多苓这样慢慢地说着,喝着茶,思绪渐渐飘入了另外的世界。
“我的所有关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都想在绘画中表现出来,都想用画笔来画。”何多苓把自己所有对文学的感觉、感情和能量转化到了绘画中。文学在他的画中渗透、流淌。“就像拉斐尔前派一样,有时候试图用画来表现一种题材,或者把某些题材作为隐喻放在画里面。但是我倾向于后者,因为我特别喜欢诗歌。我希望我的画面哪怕是文学性的,应该是像诗歌这样,很隐晦的、带有暗喻形式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那种直白的,跟小说一样,陈述某个情节。”这种隐晦的表达可以在他的很多作品——如《偷走的孩子》、《带阁楼的房子》、《雪雁》——中看出来。《雪雁》是他1980年代创作的连环画作品,除去原文学作品的语言描述,单看画面,每个插图都完全可以脱离叙述独立存在。
“我的很多作品更希望把所有这些经验、感情、修养,落实到每一笔上。”将艺术家的品格修养体现在笔意之间,同样也是中国文人画家的精神。
尽管是用油画创作,何多苓仍然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画家。
“我始终坚持绘画应该有绘画的语言。虽然我如此热爱文学,在画面上摆脱不了。但其实也没有必要摆脱文学的影响。绘画有独特的语言,就像音乐、文学都有它独特的语言一样。这个独特语言既是它的独特性又是它的局限性,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了绘画所独有的、只有用这种语言本身来表达才是最好的东西。”
永恒的精神
何多苓的作品中,人总是孤单的。他们没有特定的身份,与时代、社会好像并无太多关系。而那些忧郁、哀伤的表情又仿佛是被世界抛弃后的独自享受。
“我从来不认为美术作品是表现社会题材的最佳方式。摄影、小说、更能表现社会。美术某种程度上跟音乐比较接近,(即)从一种比较抽象的角度体现时代精神。”因此,何多苓绘画的叙事方式是以人的个体精神性为中心,强调个体情绪。当这种个体精神世界放入大的时代环境中却可以引起广泛共鸣。
“我早期作品中有人物身份的反映,与社会背景发生关联,但是,到后来画一些人物和人体时候把这些东西去除掉了。”何多苓好像从来就不是一个关心“集体”的人。“何多苓不想面对一个集体,也不想只面对自己,他选择了与另一个人面对面的旅程,在一对一的关系中,观看这个人的脸和身体,体现他(她)在画面上的形象表面和深度。”批评家朱其说。
“我的《青春》那种画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创作过一些以彝族人的形象为符号的作品,除了这些作品以外,就很少具有时代性。选择彝族人的服装是因为那种独特的、具有整体感的服饰能够淡化服装带来的时代感。后来我画人体,去掉服装以后,更没有时代性了。我想淡化服装带来的社会和时代的烙印。我想体现一种尽可能抽象的、永恒的,张力、外延,这里既有过去又有未来,这样一种形象。”
2008年“5·12”大地震以后,何多苓创作了几幅作品,与很多写实作品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用灾难现场作背景,而是一种诗意、模糊、具有暗示性的背景,人的服装也是很随意的、生活化的样子。“因为,我始终不希望自己的画局限于某一个时代。画面的整个气氛、背景人物的表情、肢体语言更重要一些。有些特征是我在画面上极力淡化的、有些是我要强化的。我更强化人的精神面貌。淡化服饰、时代背景、道具,或者是去掉它们。”
何多苓的绘画,正是用这种诗化的表达方式,将人类孤独的灵魂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