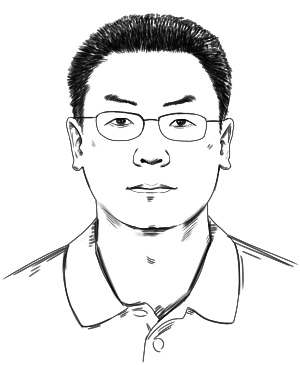|
⊙张涛 ○主持 于勇
若用望远镜来回望过去11年(2001—2011年)的中国经济,则可以用“宏观强、微观弱”来概括。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加速,经济总量问题在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性红利共同作用下已得以解决;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也越发突出,集中表现在政府占经济的比重过高、资产和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趋弱、居民的经济福利受通胀蚕食程度趋强。
此次金融危机又一次提醒我们,每当我们要举杯庆祝的时候,危机已在我们身边驻停脚步。如果我们提早察觉,那么危机就是机遇。
笔者预计2012年一季度GDP增速跌破8%的概率在增大。在前两次经济降速的时候,通胀压力并不大:1998年1月份的CPI是0.3%,2009年1月份的CPI是1%;而2012年1月份CPI则为4.5%,所以即便是未来通胀放缓趋势的不减,但同前两次经济降速相比,这一次,经济减速无疑跑到了通胀回落的前面,而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现在还不能轻言已经“软着陆”。
无独有偶的是外部投资者对于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有关外资撤出中国的新闻报道就不绝于耳,相应2011年1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短暂贬值和外汇占款连月的巨幅回落,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撤离的真实存在。
实际上如果将此次危机视为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自我调整,那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产业资本自会也相应作出调整。在当今的世界,可以说跨国公司是为数不多的能和各国政府拥有相当资源配置力的经济体,也是真正意义上经济结构调整者。对中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次危机而进入到质变阶段,此前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以及可以随意外化给社会的经济负效应(环境污染等)的比较优势已经消耗殆尽,那么相应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的资本配置调整也势在必行,因为对公司而言的硬道理就是追求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率。
笔者估算,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到1992年外商实际投资年增量超过100亿美元,到2002年超过了500亿,到2010年超过1000亿,近30年间,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累计达1.2万亿美元,相应形成的投资收益估计在2300-2600亿美元左右,投资回报率约20%-22%左右。
如今,中国的经济环境和要素结构、价格机制均发生了变化。此次危机后,全球都在搞结构调整(IMF称之为“再平衡”)。对身处在中国的国际资本而言,调整也是必然趋势,其调整的方式无非有二:投资方向不变,但需要换地方;不换地方,但需要改变投资方向。两种调整的结果均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内部调整。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近30年的外资积累,在统计数据上,使用的是成本法计价,如果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出现,再加上多年来投资回报的积累,如今要按照市价换地方,那么目前3万亿的外汇储备可能就不够(笔者的个人测算结果是存在3000美元的缺口)。如果国内资本也加入调整之列,那么数额就会更加巨大。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核心,还是中国的投资回报率,用宏观语言表述,就是经济增长,这里既包含速度,也包含质量。所以仅就目前的逆周期宏观调控而言,充其量只是“术”的层面的应对,而当前中国更需要“略”(战略、韬略)层面的应对,即内部的结构调整和资本的投资取向的调整相契合。其中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在中国经济不断货币化过程中,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搭建了一个资金融通的管道。而近30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在特定目标的融资任务应该说已经完成——筹钱的任务,而接下来留给中国资本市场的任务已经变成如何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配置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宏观而言就是找到新的增长点,对微观而言则是投资回报——用钱的任务。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