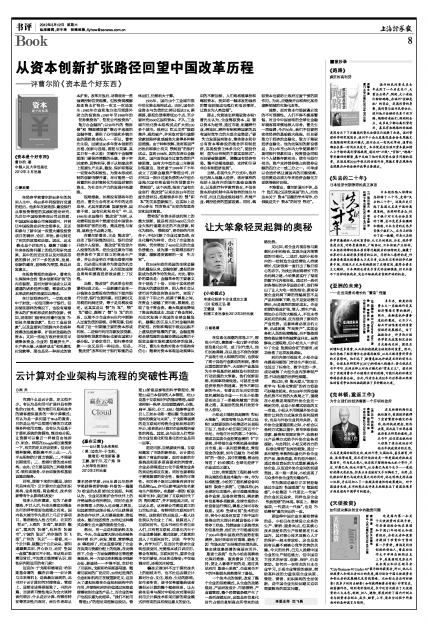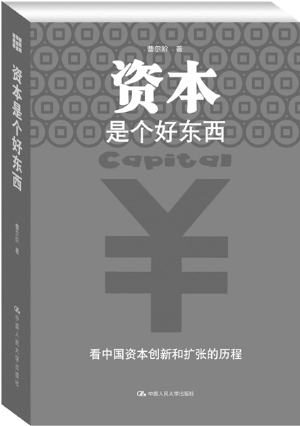|
——评曹尔阶《资本是个好东西》
⊙潘启雯
在经济学家曹尔阶80多年的风雨人生中,有60多年同投资打交道的经历。他多年在财政部、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先后任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高级顾问,并曾任中国投资史研究会理事长,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调研、论证、审批,参与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因此,这本《资本是个好东西》,凝聚了他数十年来在投资问题上的经历和研究成果,其中的历史反思以及对现实思路的探讨,对下一步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建言,显得极为厚重,极具启发意义。
在投资管理的实践中,曹老先生深深体会到“资本创新和扩张”的内在秘密,因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诸多经济问题,都尝试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加以阐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收支集中于财政,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堵塞资本的扩张和形成机制的创新。例如,财政部门就曾利用建行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出口工业品贷款”,以及直接利用预算内外的各种挖潜改造拨款等,扩张财政超收的资本;又如一些地方政府曾采用平调集体资金,企业的“基建挤生产、生产挤大修、大修挤成本”和乱挪乱拉贷款等,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政府一贯强调控制信贷规模,但投资规模膨胀即资本扩张仍一次又一次地发生:1982年企业和地方动用预算外财力的投资热;1987年至1988年的“证券集资热”、“信托公司投资热”、“地方办金融热”;以90年代的“假拆借”和“绕规模贷款”等近乎违规的金融举措,提供了办市场和乡镇企业的原始资本投入……所以,曹老先生说,回顾这60多年资本创新的历程,创新与违规,真理与荒谬,其实只有一步之差!关键在于金融管理部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善于从制度改革上理顺生产关系,激发、保护和驾驭一切资本的积极性,为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鸣锣开道,尽可能把一切闲置的社会财富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资本,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拓道路。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些年的经历,曹先生会有在本书中的这些思考。尤其在第四章“国家投资、国家干预、国有化和私有化”中,以1985年全国推行“拨改贷”为例,从功绩和扭曲两个维度论述中国资本创新和扩张的历程,兼具理性与客观,堪称全书点睛之笔。
在曹尔阶看来,正是“拨改贷”,启动了银行职能的回归,银行信贷开始介入投资。“拨改贷”和信贷介入投资的改革,把企业还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并让企业明白不能无偿使用资金,而必须以利息作为资金的机会成本再去经营收益,从而把加速资金周转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上了议程。
当然,“拨改贷”的改革也有荒谬和扭曲之处:一是新建企业在一分钱资本金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向银行告贷,银行也竟同意。而还款时又用税前利润还贷,等于是用税收偿还。这其实是以“债”为“本”,“债”“本”错位,颠倒了“债”与“本”的关系,以致不少企业在90年代中期陷入过度负债的困境。尽管荒谬,但却构成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资本形成机制。二是银行利用存款发放贷款,但投资性贷款的指标也要由国家计委分配。计委定项目,银行奉命贷款——这又是另一种扭曲。但是,“拨改贷”改革相对于银行职能的总体回归,仍然利大于弊。
1995年,国内18个工业城市推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当时,国有企业资本与负债的比例已低达2∶8,据测算,要把负债率降低20个点,至少要补充9500亿国有资本。不久,工业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扩大到100多个城市。政府以“红头文件”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并采取对银行逾期贷款挂账停息或减免欠息等多种解困措施。由于种种误解,政府高层严厉批判和禁止有关“债转股”的银行试点。直到1998年,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面临国企过度负债的严峻困境,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解困时限紧迫,政府遂于1999年下半年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对相当一部分过度负债的大中型企业拖欠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实行“债转股”。这个决策,结束了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以来长达15年的过度负债状况,把颠倒多年的“债”和“本”的关系重新摆正。这实际上是对40多年“讳言资本”历史的彻底否定和总体清算。
“债转股”在资本形成机制上的最大创新,就是将当时4600亿元企业欠银行逾期未还的不良贷款,转化为股份。“债转股”,更奇妙的作用在于,不但化解了企业过度负债,而且化腐朽为神奇,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凭空增加了4600亿元的企业负债能力,成为那一时期增加银行贷款、缓解通货紧缩的一支“生力军”。
自2008年始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创新、虚拟经济就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对此,曹尔阶的看法是:金融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创造了十倍、百倍于实体经济的庞大的虚拟经济,把人类社会从货币时代推进到资本时代,实现了交易于千里之外,结算于瞬息之间,在资金上超越了货币流、票据流,出现了电子资金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资金流通成本,加速了资金周转。而此次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正是人们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驾驭手段远远跟不上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展,金融监管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协调远远落后于现实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过,曹先生依然对资本市场抱有信心:“随着对资本客观运动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终将能掌控和驾驭资本,犹如将一触即发的强烈的雷电驯服成电弧灯和电话那样,让资本为人类造福”。
那么,究竟该怎样驾驭资本呢?曹先生认为,企业驾驭资本,是“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家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而且要破除垄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当然,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政府也已深入地融入经济,政府掌控的包括土地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资本,以及医疗科学教育资本,不但在资本形成机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已发成规划城市、布局产业、调控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驾驭资本也要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的副作用。为此,应继续开启和深化某些垄断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诚然,面对资本市场波谲云诡的不可预测性,人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对当今中国面临的全球化金融环境客观审慎地深入思考。曹先生一再强调,今后30年,我们不但要把实体经济的基础做大做强,而且要致力于经济的金融化,致力于驾驭经济金融化。他为此谋划的新设想是,在10年至15年内力争使票据市场同银行贷款相当;投资基金同银行个人储蓄存款相当;债市与股市相当;资产支持债券能占到债券总额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考虑以合适价格让渡国内的巨额储蓄,但前提是必须力争在经济金融化方面获得较好回报。
不难看出,曹尔阶退而不休,是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国”的人。而他这本关于“资本”话题的学术写作,仿佛就是关于“资本”的时空“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