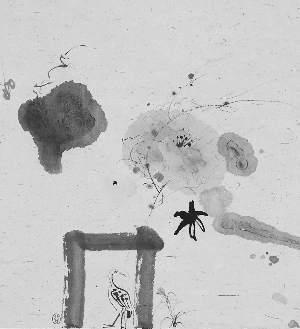| ||
| ||
|
⊙记者 邱家和
水墨艺术,土生土长的本土艺术,被一百多年来引入的西方艺术所激荡而不断蜕变,近年来成为艺术市场的新热点。从标榜学术的双年展,到炫耀财富的艺博会,水墨都成了焦点。恰逢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与多伦现代艺术馆发起“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不仅聚集了许多艺术家、策展人参展,还请到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举办论坛,让我们有机会从作品到观念澄清水墨艺术这个概念。
朱屺瞻与多伦:新水墨大展
上周末,“水墨纵横——2012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的学术主题展“回到地域——水墨与美术史”在朱屺瞻艺术馆开幕。展览规模宏大,同时在朱屺瞻艺术馆和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举行。展览选取了清末、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八五新潮”及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8位艺术家:朱屺瞻、张桂铭、贾又福、王川、广曜、宋钢、王纯杰、雷虹,以现代水墨和当代水墨的互动以及艺术家个案的形式展开美术史内部的对话,梳理中国水墨发展至今的历史线索。与此同时,一起开幕的还有上海新水墨艺术基地特展,由刘国松、陈家泠和仇德树这3位上海新水墨艺术基地创始人参展。
展览主办者认为,“水墨”不仅是一种媒材,它是中国传统价值和意义的符号,任何改良或者革新的方案都必须直接动摇“水墨”背后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意识形态才可能导致其真正的演进:从林风眠、徐悲鸿等在引入西方绘画方法,到新中国艺术家们为了表现新时代的气象打破原有的笔墨程式,到70年代末出现现代“水墨”,逐渐成为被艺术家自由使用的媒介,在到90年代以来,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等新的艺术现象不断衍生,带来水墨领域内新的思考维度。2005年起每年举办的“新水墨”大展,已经成为每年一次检阅水墨艺术成果的盛大活动,而今年最大的特点,是国际论坛极其引人注目的主题:“回到地域”。
国际研讨:回到地域
在5月26日持续一整天的论坛上,朱屺瞻艺术馆的艺术总监陈九在论坛上指出,从2005年开始朱屺瞻艺术馆和多伦艺术馆联合举办了上海新水墨大展,已经持续8年,推出了很多中国新水墨艺术家的成果,借助社会的力量共同打造了新水墨基地。上海不仅有陆家嘴那样的新都市景观,也是中国都市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而上海的新水墨就是这个都市文化的活体。
学术论坛上引人注目的是一众国际学者,如来自印度的学者帕罗-戴夫-穆克赫吉(Parul-Dave –Mukherji)、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包华石(Martin J. Powers)、 詹姆斯·埃金斯(James Elkins)与蒋奇谷。他们从水墨艺术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气”的关系、与“笔触”的关系、与观看方式的关系,展开他们的论述。而国内学者中央美院教授殷双喜则梳理了建国初期“新国画”的成型;南京艺术学院顾丞峰则考察了“新水墨”概念的演变。四川美院王南溟、北大教授朱青生则在发言中直接回应了海外同行的观点。
作为论坛的主持人之一,朱青生认为,水墨艺术的探讨涉及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区别问题,比如外国学者看中国水墨是当作绘画来看,但一个中国人会把它当作书法来看。观看方式的差异,还涉及哲学根源和思想方法的根源。他强调中国的思想方法不是来自于逻辑,而是来自于另外一套思考问题的方法,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经典《易经》所体现的——各种因素调节在一起取得了一种折中的效果:许多事情的发生不像西方逻辑学所强调的那样有因果关系;同时,同样的原因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他表示,由于这种根本的差异引起世界美术史学会的重视,将于2016年举办的下届世界美术史学会大会将在中国举行。
埃金斯:世界上主要的边缘艺术
知名学者詹姆斯·埃金斯认为,中国的水墨画是世界上最边缘主要的艺术。“边缘化”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通常来讲水墨画在一个展览上会有单独的展览空间;第二,在西方的一些学院里大家关注的都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而不会关注水墨画艺术的发展;第三,水墨在中国的艺术史上的一些表现还有它当前的现状。如果要给水墨画一个新的定义,涉及四个要点:第一不应该因为它使用水墨来做定义;第二不应该以笔法来定义水墨画;第三点不应将水墨本身作为一个支持和论据来给水墨做定义;第四不应用技巧来形容水墨画的定义。他认为水墨画是取决于它受到历史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它的容量,也就是需要多种历史的沉淀,多种多样相应的信息才能对其作出更好的解释。
他表示,正是因为如此,水墨画并不容易融入整个的国际艺术品当中。有的观众不想花很长时间去充分理解作品的内涵,他们可能只愿意花费几分钟的时间。这也就是水墨画迟迟不能进入国际市场被观众理解的原因。从传统的西方美术市场看来,中国的水墨画看起来那么无聊,既不够实验性也不够前卫,不包含一些热议的话题。要使中国的水墨画在世界上真正有所建树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蒋奇谷:回到水墨画
论坛的另一位主持人蒋奇谷,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既是一位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也是一个策展人,同时还是一位艺术家。他在论坛上大声疾呼,现在水墨变得错综复杂,应该回到水墨的出发点,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回到水墨画。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水墨艺术不是水墨画,而是一种新的艺术。比如在最近看到的一个生物水墨装置作品《稻田里的故事》,由装置与视频构成,后者用数码显微镜显示生活在水稻田里的草履虫,他不禁要问:这个作品与水墨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称它为生物水墨作品?在当下水墨艺术里面,像这样的水墨艺术非常多。但是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仅在媒体上,更加在观念上面和水墨画分道扬镳,它们和水墨画的联系牵强附会,已经完成了水墨画的否定,并从水墨画里面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态。水墨艺术不是水墨画;水墨艺术没有给水墨画带来促进和发展;我们要回到水墨画。
有趣的是,蒋奇谷与他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画的学生,在上海徐汇艺术馆联手举办了一个画展。在画展上,蒋奇谷旅美25年来创作的水墨画,也许是他的艺术观点的最好说明。比如蒋奇谷的作品中有一组人体作品,用中国画的笔法来画人体,而在手法上又是中西混杂的:人体,用纯粹的中国画线条方法画出;其他部分则挪用了西方的表现元素。又如其命名为“宁静致远”的系列作品,可以笼统归入“山水画”的范畴中,在画面的表达上更多地调用了西方所熟悉的中国观念和元素,将中国山水画的观念和抽象表现手法糅合。而在其“庄周梦蝶”系列作品里,灵动的线条、敏感的色彩、大开大合的构图与清醒雅致的气息是艺术家的擅长,但也揉进了现代构成元素。有人说,蒋奇谷的线条是灵动的,这种灵动既是因为他擅长提笔,也是因为他善写长线。这种线条配合着扎实的造型能力,就能使线和形浑然一体而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在展览现场,蒋奇谷那些金发碧眼的美国学生的水墨作品煞有介事,当有人问特地赶来观看的詹姆斯·埃金斯,蒋奇谷师生的作品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埃金斯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区别正在于画面上的线条。他所强调的正是水墨画中的“笔法”的不同。也许,这才是蒋奇谷大声疾呼的“水墨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