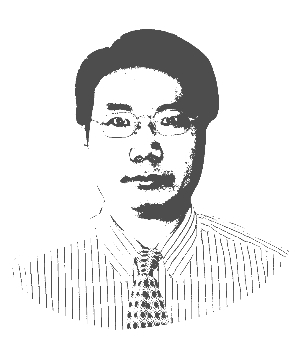|
袁东
“我从事政治是因为善恶斗争的存在,而我坚信善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撒切尔夫人说这句话时,她已将自己作为“善”的化身了。恐怕几乎所有人都会有撒切尔夫人的这种心理和言说,然而,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恶”却是以“善”的名义铸成的,在政治生活中更是如此。
何况,人性既有善也有恶。能否通过欧文·白壁德强调的那种“洞穴内的斗争”,在自身层面上完成善恶较量,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个极大的疑问。更为虚伪甚至荒唐的是,很多时候,人们会用“善”去包装修饰一个彻头彻尾的“主观故意恶”,尤其在公共生活中。
英国伟大的讽刺小说作家斯威夫特曾说过:“有时,动物也会堕落成人。”这句话在两个层面上是有意义的:其一,动物的欲望仅限于自然需要,人的欲望则无限,没有节制的贪婪催生层出不穷的恶。所以,白壁德说:“具有无限倾向的人,并不会变成野兽,而是会直接变成恶魔。”其二,动物的恶是直接显露,没有伪饰,更不会南辕北辙地去说一大堆动听的话;而人却总为自己的恶寻求一层层善的虚装,甚至将真实意图的恶说成是直接的善。
即便是切实出于善的主观意图,也不能确保结果就不是恶。美好的善的意图与善的结果之间,还隔着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需战略的设计与实施。问题是,就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而言,过于雄心勃勃却并不合乎理性的目标,随之而来的脱离自身比较优势的战略设计与实施,由此形成的恶果严重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类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
20世纪下半叶,那些刚获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出于良好愿望而迫不及待确定了雄伟的“赶超型”经济战略,牺牲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阶层利益,沉浸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优先投资。结果不仅没有带来事先宣扬的改善和“赶超”,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并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和经济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以至重大破坏。对此,林毅夫教授在最新出版的《繁荣的求索》一书中,从经济学的逻辑给出了总体上的汇总与分析,所议所论,值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领导者以及发展经济学家细细咀嚼。
就是那位视自己为“善”的化身的铁娘子,在执政后期也越来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拼命煽动自以为是“善”的翅膀,却划出了一道恶的阴影。以“社区费”名义征收的“人头税”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普天之下的众生,谁都不是上帝,如若不谨慎,却很容易成为恶魔。所有道德伦理固然倡导人们尽量趋向发挥人性善的一面,但是,如果将善夸大到极致,甚至以“人性本善”为逻辑起点与归宿,特别是将自己视为善的化身,极力宣扬过于美好的愿望,一切的一切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和幸福,口口声声宣称服务于他人与大众,这就格外值得警惕了。这不仅是极大的虚伪与做作,而且,这种性情一旦没有节制和有效的外部制度制约,必然迈向无限权力意志追求中的狂妄恣肆,在忘乎所以中酿成公共生活的恶果,最终也吞没了他自己。
一味的服务意味着一味的控制。尽量杜绝恶念的同时,对于善意也要适当。理性的控制和权衡,不仅在个体层面上是需要的,对于公共生活亦为必需。就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说,阶段性设计和调整既是一种宏观经济决策,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决策者不应让那种美好的善的意图遮蔽了理性的视野,而应当注重经济思想的指导,确定合乎理性的、有节制的适当目标,认清并遵循自身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以此来设计和实施经济战略,才可能结出善的果实。
文明的进步,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狂热的行动,需要的是目标和价值合乎理性。这种理性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持,但显然不是主要靠伦理道德所能确保的。公共生活中的理性,主要应诉诸能有效约束“恶意”并能有节制地激励“善意”的合适的制度体系,这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外在的激励和控制。
任何人都是一个善恶结合体,文明的进程就是抑恶扬善的过程,这需要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的恰好组合。文明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束缚。如果像英国那位最独特和最有争议的作家劳伦斯那样仅仅将文明视为一种束缚,那只是过于自私和本能性情不节制的偏激。就像美国理性私利主义伦理学倡导者安·兰德所概括和倡导的,最好状态是有德性的自私。自私有可能完全遮盖了德性,而德性无论何也遮蔽不了更替代不了自私。一切漂亮的词语都不是事实,只是事实和想象的某种组合,仅具有限的引领效应。由此,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也就不能相互替代,前者位于私人领域,属于个人建设,需要的是一种人文主义教育和修养,甚至宗教信仰;后者位于公共领域,属于社会和政治建设,仰仗的是制度化的权力共享和制衡。
理性的方向是,既要防止以公共“善”的名义放纵个体和小团体的恶,也要警惕那种挥发无节制的个体“善”却导致公共性恶果的可能性。(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