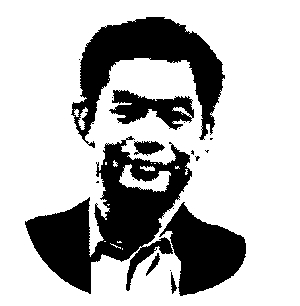|
中国经济已到了必须紧紧围绕战略转型提升增长质量的关键时期。在中央政府“稳增长”的基调下,地方若为了拉抬本地经济指标而再次“保增长”,只会推高系统性风险,加剧失衡。因此,在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必须厘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执行力。
在李克强总理将宏观调控定调为“区间管理稳预期”之后,各省区纷纷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从有关会议的内容来看,几乎所有省份都提到要通过稳投资来稳增长,有些省甚至提出保增长。因此,如何贯彻宏观调控新思路,消除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便成为当务之急。
从政策导调与执行背景来看,今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与复杂程度可能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大国的都复杂。诚然,伯南克、雅各布·卢等美国经济政策的操盘手们再难像当年的格林斯潘和鲁宾那样有足够政策空间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但美国基于金融霸权而拥有的全球性金融红利和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却是中国难以企及的。同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在为如何走出“失落的十年”乃至“失落的二十年”不断祭出各种经济政策(包括新近的“安倍经济学”),尽管成效不彰,但早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其拥有的庞大海外债权和一流科技能力,也让中国难望其项背;至于多年来保持经济增长高质量的德国,更值得中国虚心学习。
可以说,今日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程度,经济战略转型的难度与跨度,超出了世间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设定。80年前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基本上是对凯恩斯信条的照本宣科,即政府“必须做些事情”来鼓舞人们的信心,无论是通过直接救济,还是兴建大型工程。但今日中国经济问题早已不是政府“必须做些事情”就能解决的了,需要克服诸多约束瓶颈。众所周知,“十八大”报告中已给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路线图,但从这些年来重大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往往在需要落实到执行层面时,便长时段停留在纸面上。这不仅是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往往不一致,还由于现行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只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职权划分的总原则,并未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致使地方政府的职权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央政府职权的翻版,各级政府职权与职责同构现象严重。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有的事权以及剩余权力的归属并不清晰,政策落实与执行出现更多的模糊空间,地方政府会充分利用其事实上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或者利用中央政府的授权,最大化自身利益。甚至出现一个地方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政策优惠承诺,其他地方随后跟进并提高要价,造成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妥协与过度放权的现象。此外,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呈现逐年下降之势,而其承担的公共服务支持则在不断增加,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热衷于土地财政的收入增加,弱化公共服务功能是很自然的逻辑安排。由此造成地价飙升、房价居高难下以及地方债的不断膨胀,尽管是中央政府不愿看到的,却是地方与中央非合作性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在地方政府看来,即便是集聚了太多风险的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最终演变成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到时候一定会进场干预。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至于地方政府扭曲中央政府的政策红利释放,在投资领域更比比皆是。
事实上,即便是极富刺激色彩的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还是非常关注经济结构调整的。从那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内容来看,短期内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在中长期内,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只是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并未深刻理解并贯彻其中的核心精神,因而没能坚持在转变经济增长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等重要环节上下大力气。结果,凭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尽管成功地避免了类似日本那样的经济雪崩,但付出的短期代价与承受的中长期风险,现在让我们感觉到了越来越强烈的阵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这几年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表面增长的;至于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以及由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显然并没有在各地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考虑之中。
今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文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普遍被视为是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的优化政策,但落实到执行层面则另当别论。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今年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将在保持财政赤字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着眼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做一些政策微调,更多精力将用于推动下一轮财税改革。但来自各地公布的投资计划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超过20万亿。如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
中国经济发展已到了必须紧紧围绕战略转型这个核心命题来提升增长质量的关键时期。在中央政府“稳增长”的基调下,地方政府若为了拉抬本地经济指标而再次“保增长”,只会推高系统性经济风险,加剧内外经济失衡。因此,在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必须厘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执行力,以消除地方与中央的非合作性博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