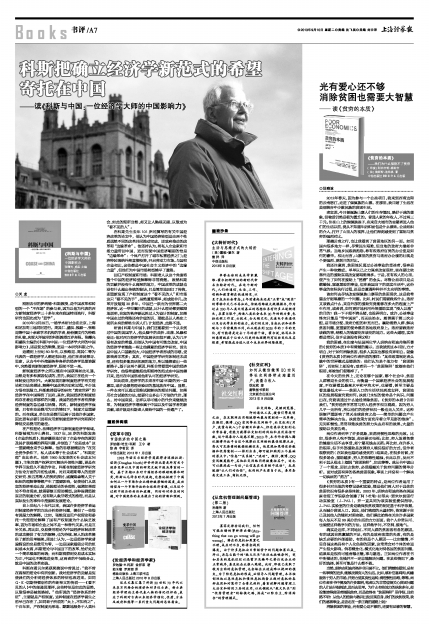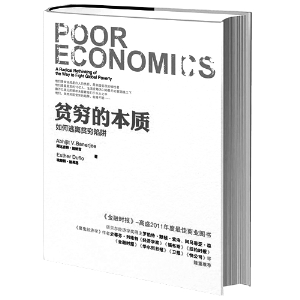消除贫困也需要大智慧—— 读《贫穷的本质》
|
光有爱心还不够
消除贫困也需要大智慧
—— 读《贫穷的本质》
⊙汪晓波
2012年春天,因为参与一个公益项目,我来到西南边陲的云南怒江,走进了傈僳族的山寨。在那里,我目睹了生活在美丽峡谷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生活。
老实说,今日傈僳族山寨人们的生存境况,略好于我的想象,但物质仍然是极为匮乏的。普通人家的年收入,不过两三千元。住在山上的傈僳族孩子,在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进入他们的生活以前,竟从不知道牛奶和面包是什么滋味。公益组织的介入,打开了山里人的视界,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富裕与贫穷的强烈对比。
那趟云南之行,也让我看到了贫困地区的另一面。如同国内很多地方一样,尽管民生艰难,但当地的政府大楼却非常气派。当地乡民跟我抱怨,称有些政府官员的办公室是如何的豪华。相比而言,山寨里的贫穷与政府办公楼的壮观是个更强烈、更刺目的对比。
我还注意到,贫困地区通过公益事业的受益者,很容易产生一种依赖症。单单以己之力谋求改变现状,实在要比依靠外边的援助实现改变要艰难得多。于是,在有些人的心里,便产生了如何在援助上“挖潜”的念头。尽管公益项目是点燃蜡烛、驱逐黑暗的事业,但在我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这份事业的实际执行过程,还是会遭遇种种并不太光明的事情。
该如何去尽快改变傈僳族山寨里的贫困现状,这是我希望去仔细琢磨的一个问题。比如,村民们需要做些什么,政府又该做点什么,来自外部的援助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作用,或者说,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援助实现“授人以渔”的目的?我一下子理不清头绪,也没弄明白。或许,公益事业终究只能是“雪中送炭”,而无法治本。慈善属于第三次分配,是市场分配、政府分配的补充而已。襄助弱势人群、解决贫困问题,更重要的使命落在各地政府身上。政府要做政府该做的事,纳税人的钱要花在该花的地方。这些大道理,实在都是常识,似乎总该没有异议吧?
我的困惑,在印度与法国两位学人班纳吉和迪弗洛所著的《贫穷的本质》中有清楚的揭示。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方才明白,对于如何消除贫困,很多人其实也都没有弄明白。就像《贫穷的本质》的两位作者所说的那样:“某些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世界模式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有‘贫困陷阱’,而实际上却没有;或者另一个‘贫困陷阱’就摆在他们眼前,却被他们忽略掉了。”
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中,贫困人群都是社会的伤口。而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仅要看其最高水平和平均水平,也要看,甚至主要是看其最低水平——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到底怎样,贫困地区的发展程度究竟如何。扶贫乃永恒的使命是个共识。问题出在,究竟该通过什么途径消除贫困。《贫穷的本质》告诉我们,“贫穷经济学常常与穷人经济学相互混淆,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也无人关注。这种误解严重影响了消灭全球贫穷之战——简单的问题会产生简单的解决方法。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无知和惯性,常常导致扶贫的努力失去应有的效果,大量的援助以失败告终。
两位作者列举了许多现象,来说明惯性思维的无效。比如,很多穷人吃不饱饭,却还要买电视;比如,穷人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宁愿花钱去买药;再比如,在许多人的眼里,似乎外部援助是改善穷人境况很好的方式,但作者观察到的(亦如我也隐约感受到的)结果是,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场合,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长此以往,反而不利于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陷阱”,如此等等。我从书中读出了一个理念,即抗击贫穷,必须超越关于贫穷问题的简单分析。面对成因有异的各类贫困现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解决一切疾病的“药方”。
《贫穷的本质》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两位作者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和实验,那是他们两人对于具体的贫困状况有很多亲身体验。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建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因此,他们梳理的大量材料,皆来源于自己及其他人的随机对照实验。他们据此始终在关注许多国家每人每天不足99美分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个人非常认可、也偏爱这样做学问的方法。这样做学问,不空洞,接地气。
确实是这样,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贫困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或因自然禀赋的不足,有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有的是缺乏必要的外部援助,有的则是个人原因——比如懒惰、不思自强这类具有个人化色彩的因素,这常常会对个体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倘若概念化、模式化地对待各国的贫困问题,结果却是很有可能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正如两位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花钱并不一定总能解决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选择,甚至可能是什么都不做。
当然,班纳吉和迪弗洛并非只破不立。他们清楚地看到,总有一些事情的进步,能够改善穷人的生活。比如,填补信息鸿沟;构建服务于穷人的市场,并努力使其良性运转;清理惯性思维,等等。两位作者在书中提及的许多案例,笔者以为非常值得关心贫困问题的人们去仔细阅读,进而去思考。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扶贫多年,却没能使得贫困者摆脱贫穷,而是始终在“贫困陷阱”里徘徊,且前路不明?从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出发反观自身,我们的扶贫政策,我们的慈善事业,是否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呢?
消除贫困的事业,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