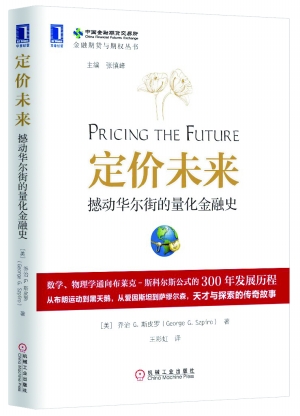量化金融研究缺失了什么
| ||
|
——读《定价未来:撼动华尔街的量化金融史》
⊙毛志辉
谈及“量化金融”,人们往往会存敬畏之心,因为若无坚实的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基础,难以涉足其中。的确,在量化金融发展史上,从事相关研究的,都堪称是勤奋的、善于创新的天才。这些传奇人物的成长经历及科学探索历程,往往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因此格外引人好奇。美国数理经济学家乔治·G·斯皮罗的《定价未来——撼动华尔街的量化金融史》所呈现的,正是这么一张期权定价理论发展史上的群英谱,他们的故事,自有诸多让人心潮激荡的迷人之处。
在过去数百年间,对期权的定价,投资者通常只能依靠简单的直觉来预估,没人知道决定期权价值的究竟是什么因素。遍布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和金融天才们才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求索,最终成就了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段段传奇。
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是金融界的一场革命,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在内的新兴衍生金融市场的各种以市场价格变动定价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虽然时至今日,对这一模型的褒贬、演绎,仍在学术界、金融界延续,但期权定价理论已被公认为金融学在20世纪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之一。迄今,人们尚未找到超越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方法。
这个故事,源头可追溯到16世纪30年代的荷兰郁金香事件。当时,荷兰大部分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郁金香抢购狂潮,并最先利用了期权交易。由于郁金香花的价格异常高昂,种植人便与投机商们商定作卖出期权。最终,当郁金花市场崩溃时,许多投机商都无力履约,巨大的债务危机严重损害了荷兰经济。
在阿姆斯特丹从事投机生意的约瑟夫·德拉维加,在《乱中之乱》中完成了对期权交易的首次描述。这使他成为金融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而他的写作,仅仅出于娱乐和警告的目的。大约两个世纪后,与德拉维加身份类似的经纪人助理雷格纳特,靠自学发展出了一套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于1863年出版了被视作现代金融理论的“奠基作品”的《概率计算和股票交易哲学》。雷格纳特在书中第一次用公式表达了一个数学规律:股价的差值与所考察的时间周期的平方根成正比。
1900 年,法国学者路易斯·巴舍利耶在博士论文中抛开了对金融市场的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用概率论建立了金融市场价格的随机游走模型。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用理论模型研究期权定价问题的论文。遗憾的是,由于源自他人的傲慢与偏见,巴舍利耶的杰出理论模型沉睡了60年。
同巴舍利耶一样,一位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也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观察过波动。布朗用显微镜观察悬浮在水中的花粉时发现,那些微粒一直在高速震荡运动。后来这一发现被命名为“布朗运动”。接下来是爱因斯坦,对物体在液体中因为扩散过程而不规律运动,他通过数学处理,提出了一个关键论断:“位置的均值与时间的平方根成正比。”这个结论,恰与40年前雷格纳特对股价变动的分析完美契合。
探索真理的路上总会有许多志同道合者,尽管他们未必相互熟悉。除了爱因斯坦,波兰物理学家马利安·斯莫鲁霍夫斯基,法国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让·佩兰,瑞典化学家特奥多尔·斯韦德贝里等一批划时代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布朗运动做出了理论解释,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随机游走的理解。虽然他们大多并没有关注布朗运动潜在的应用领域——金融市场,但却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对金融学的量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工作又都不够严密,甚至没有给出这一不规则运动的数学描述。
是概率论和积分学的发展,为期权模型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当斯皮罗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伯特·维纳,法国数学家保罗·列维、亨利·勒贝格、艾尔弗雷德·内马科、亨利庞加莱、沃尔夫冈·德布林,前苏联数学家安德雷·柯尔莫戈洛夫,德国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日本数学家特奥多尔·伊藤清等一批数学天才在相关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环环相扣、一一介绍时,不免让人觉得所有的学术进展似乎都在冥冥之中注定,有一种在等待着一个“修成正果”时刻到来的感觉。应该承认,巴舍利耶突破数学和经济学理论限制的首次尝试,之所以能在60年后得到学术界的“追认”,离不开理论界、数学界对布朗运动和随机性解释的发展。
巴舍利耶的超前性工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被耶鲁大学统计学家伦纳德·“吉米”·萨维奇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重新发现。萨缪尔森不遗余力地在经济学专业圈内传播巴舍利耶的成果,此后,金融学家才真正从这篇文献上直接续上了期权定价理论研究的“香火”。
在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提出之前,萨缪尔森、卡斯·斯普瑞克、爱德华·索普、詹姆斯·博恩斯等人,都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期权定价模型。虽然他们的探索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一系列文章却奠定了现代数理金融的基础。在萨缪尔森的影响和带动下,麻省理工的三位学者罗伯特·默顿、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几乎不约而同地向着期权定价研究迈进。
颠覆性革命发生于1973年。那一年,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发表了关于期权定价的经典论文《期权定价与公司债务》,默顿则发表了《理性期权的定价理论》。他们提出的定价公式与其他期权定价模型不同,期权的价格并不依赖于似乎相当重要的投资者对股价变动收益的预期。他们通过建立产生确定收入而与未来股价无关的对冲证券组合,获得期权的均衡价值。因此,不论股票收益如何变,不对这一对冲证券组合的报酬产生任何影响。他们的模型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方便精确地确定期权价值、控制风险的手段。1997年,斯科尔斯和默顿凭借这个期权定价模型捧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布莱克已于1995年辞世,遗憾地错失了这一最高荣誉。
期权定价理论所带来的金融学方法上的革命已为大家所公认,也成为金融学方法上的分水岭。但正如斯皮罗的书中所展示的,金融学的方法论从以哲学思辨和历史描述为主,过渡到以定量描述和模型检验为主,是建立在自德拉维加以降的众多天才的共同努力之上的。事实上,布莱克、默顿和斯科尔斯的贡献远远超出了衍生商品定价。他们这套方法已被证明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不仅可以用于投资项目灵活性的估价,也可用于保险契约和担保估价;在金融经济学科内外都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自金融学理论确立以来,学者们从事金融学研究的“初心”往往都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如巴舍利耶以及早期的学者起码在主观上还把理论与模型作为科学来追索;至于爱因斯坦、郎之万等理论大家,以及庞加莱、沃尔夫冈等沉迷于数学的学者,清一色都是在做纯粹的研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桥头堡”的麻省理工的精英们,大概也没有多少功利目的。
然而,与这些“前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主流学界的金融学家们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已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金融学研究似已“迷失方向”。经过长期的争吵和经验检验,量化模型和现实存在的差距已人所共知。在这种背景下,多数金融学家研究的出发点往往已不是为了科学,而单纯为了利益。金融学理论因而也渐次沦为金融学家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有的量化模型虽然很糟糕,但依然能让学者扬名天下。因此,近年来,对量化模型的批判声音日益尖锐,著名金融学专家帕布罗·特里亚纳甚至为此著成《教鸟儿飞行》,彻底批判和否定近年来以数学金融学为基础的金融理论和模型,并揭穿出那些挥舞文凭、深藏不露的专业人士,是如何为一己私利蒙蔽世人、运用理论为接踵而至的风险辩护的。这无疑是在为“迷失方向”的金融学研究敲响警钟。
这就是今天量化金融研究面对的两难困境:注重现实性就做不出模型,构造模型就无法满足现实性。对此,在反躬自省的同时,回望金融学发展史上那些学术大师们的身影,或许从他们的人格和经历中,能让金融学研究者们明白自身到底缺失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