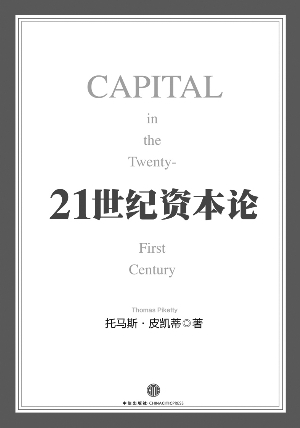中国道路抉择
|
——李迅雷、刘胜军、邵宇与马斯·皮凯蒂对谈《21世纪资本论》
中国贫富差距拉大主因不是r大于g,而有很多复杂的体制性原因
李迅雷(海通证券副总裁):
今天与托马斯·皮凯蒂直接对话,是个太好的机会。《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有近700页,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基本逻辑看懂了: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超过GDP回报率,也超过收入薪酬回报率,这使得贫富差距再拉大。
我在2010年前后过写了好几篇有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报告。那个时候我们面临两年4万亿的巨大投资,投资增加使资本在这时又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一批人因为获得大量投资,财富增长很快。另外一方面,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近年来收入分配的改革做得很不够。皮凯蒂强调中国透明度比较低。我在这里可以给他提供两个数据,一个是我们存在所得税的征税困难,我不知道法国个税占整个国家税收的比重是多少。或许有20%至30%,美国可能在40%左右,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财政税收比重大概在6%到7%之间。这实在太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效征税,这是个大问题。假定中国人均GDP过去30年中每年增速在10%左右,资本回报率增速要超过10%,在这个过程中差距显然是拉大了。
从2010年起,我也在研究中国的灰色收入问题。我从统计年鉴上面发现两组数据,一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抽象调查数据,从中获得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上中国的人口,就是总收入。另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线流量表也有个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我把这个总额累加起来,再减去它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据此,我当时推算结果是,2009年我国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约7.89万亿,我认为这么大的缺口就是灰色收入。
最近发改委有个官员被从家里被搜出两亿现金,有两吨重,这说明这一类灰色收入,确实还是要有个估算,政府应采取措施,对富人有效征税。我没有得到具体数据,有些人提出来的数据是,个人所得税,我国60%是向工薪阶层征收的,而美国超过70%是向富人征收的。
我们正在推行国企改革,国家债务越来越高,地方债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累加起来,有些说法50%,有些说法70%。负债对应的是资产,负债越多,意味着拥有资产的一方,资产增值也会很快。我们的政府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公共资产,将来如何分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石化第一单成立中石化销售公司,把这些股权卖给了谁,我看不少富豪都参与了。另外,我们把最值钱公司在海外上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携程等等,都在海外上市了,海外投资资产回报率可以很高。如何让普通老百姓能分享这些资产的收益,是个很大的问题。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我们关注的角度应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收入差距主要就是皮凯蒂讲的r大于g的问题,但中国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主要不在这里,而有很多复杂的体制性的原因。我能想到的几个因素是房地产、股市、央企垄断。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现在城市中产阶级,如果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房子,就变成了“房奴”。房地产就是个巨大的财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获得大量的土地出让金,还转移到房地产开发商。很多房地产开发商背后代表是权力资本。
美国很多投资者,很多养老金投资股市,回报率是美国股市不断创造的价值,如果你能有长期投资,能获得比较好的回报。但在沪深股市,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主要是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很多公司挂牌时已完成了套现。有些通过各种手段上市的企业,背后有很多权力资本。比如说PE腐败。
垄断定价一定比完全竞争的市场要高,这个高出这一部分就是消费者剩余。简单地说,每个月可能给中国移动多付了几百块钱,如果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你就不用再多花几百块钱付那么高的电信费,我们的金融,还有很多行业的企业垄断,也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非常大的因素。
还有,政府掌握了太多权力,意味着市场交易成本加大,我们现在都很关注中小企业负担,中小企业税收高,其实,很多中小企业用于寻租,用于搞定政府官员的成本有时比税还高。这从本质上来讲也是财富的分配。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灰色收入,因为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太大。这些问题不解决,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而且与美国不一样,我们的贫富差距不是由企业家的不同天赋造就的,乔布斯的致富是因为发明、创造了深受欢迎的好产品,而我们不少企业家的财富是不能见光的。
说到税收,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说所得税,我们都知道累计税率,但真正交所得税的人都是穷人。中国很多白领交了最高的税率,每年交的税可能比很多亿万富豪交的还要多。所以,真要减少贫富差距,关注重点不应是所得税。如果我们想真正要从税收角度去解决收入差别问题,那该尽早开征遗产税。很遗憾,遗产税到今天都还没有推出。媒体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已偷偷把财富移交给子女了,已逃过第一轮遗产税。
至于皮凯蒂讲到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我觉得在当前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焦点,我们面临的焦点还是怎么限制政府的权力,约束垄断,消除腐败,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合理。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要从数据上辩驳皮凯蒂这本书几乎不可能,皮凯蒂没有太多理论,他就是列出一个事实。《21世纪资本论》整本书只有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过去300年中,只有二战以后的20至25年间名不符实,其他时间都可以名至实归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到70年代以后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年代。这段历程之前,战争和革命摧毁了财富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从1890年到1910年的一战前被称之为“镀金时代”。现在无非是新自由主义回到整个政策或世界核心。从某种意义说,世界正在回到原来的所谓“镀金的时代”。
但回过头来,把这个现象投射到中国,问题就大了。中国这样的发展过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国这35年高速增长,可定义为原始积累,它运用三个剪刀差来完成。第一来自于农产品和工业品利润的剪刀差。第二来自农民用地特别是房地产土地用地的剪刀差。第三是一级市场原始股跟二级市场PE突然变成20倍、60倍二级市场之间的剪刀差。这是我们财富来源或者说财富分化重要基础。
若问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首要因素是什么,刚才李迅雷说的是灰色收入,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日本的情形。因为在中国最常见一种财富分化的方式是这样的,比方说在做城市化时候,征了农民一块地,批发可能是400万、500万,盖了房子又获得更高增值,这是把大家财富拉开最主要因素。我们大致做了个测算,数据没有做得那么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很快的,现在私人部门净财富有260万亿元,但每年广义货币M2增长20%,所以我们得问,究竟是资产泡沫的高速增长,还是不平等土地与户籍制度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因,只有找到这个主因,才能对症下药。
中国的税收制度要注重计算不同收益群体的税率
托马斯·皮凯蒂(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21世纪资本论》著者):
我赞同各位的观点。当前中国所面临很大的问题是灰色经济,包括腐败。当然还有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现象。如果累进所得税能不断使我们的税收体系更加完善,也会获得更好的透明性,那将会使个人所得税公开,你就会知道你的邻居,其他熟人缴纳税收的情况,大家可以互相对比各自的生活水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控制腐败的方法。
如果没有这种公开的个人信息,那可以让政府每年发布国家的以及地方的纳税人的相关数据,尤其收入比较高的纳税人的纳税情况。我认为这能有助于更合理地向那些收入很高的人征税。比如一年赚500万和1000万的人。我们可以细分这些数据。从地方层面上来细分纳税群体,就可以暴露税收制度管理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税收制度要对各个不同收益群体的税率作具体计算。
当然,征遗产税很重要。我认为战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是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当时的西方国家发展情形与现在很不一样。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也不一样,完全的自由市场,也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我认为这个特例都是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有战争,影响了当时的税收改革。当然这不意味着难以改革,并不代表改革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借鉴历史。
税收改革肯定会面对很大的障碍,中国要征收遗产税,可能会经历很多政治上的探讨。在西方,征收遗产税花了很久时间,在法国、德国有议会辩论,那些精英说他们不需要征收遗产税。如能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以更和平的方式推进并获得更大的透明度,或许中国的税制改革会做得更好。
说到财富的公共转移和私人转移,在有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有些人告诉我,如果看一下初级收入,美国最底层人的收入增长很慢。但我们看到在90年代到2000年美国底层人的收入有很大增长。财富转移的确带来增长,但不能高估。如果需要通过这种财富的转移来实现最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我认为有效的办法在于投资于教育、就业。但要实现最底层的人的收入增长,仅通过财富转移不是很理想的。
在现实中,最大的转移是收入的转移。所以,要计算出这些转移的价值给接受者所带来的价值,其实很难。因为有些涉及医疗,有些涉及教育。比如说在公共养老金方面,穷人富人的寿命增长期也不一样。我们看一下私人财富的转移,比如基金、慈善基金等等,我在书中就谈到了这一点。在美国,很多亿万富翁慷慨捐赠,看一下哈佛大学的捐赠,从80年代到2000年,这类捐赠所带来的回报超过了10%。我也研究了哈佛大学毕业生对母校的捐赠,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捐赠其实少于他们财富总量的0.5%。所以,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些亿万富翁慷慨捐赠。虽然他们有时候的确很慷慨。私人捐赠不可能取代公共的税收体系。
如果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话,我们需要一些公共资源,不一定要100%的拥有率。比如,意大利把学校这些公共财产卖出去变成公共负债,因为学校要给私人租金,有些人很惊讶。但是因为政府负债,纳税人就获得这些利息收入。大学只占1%的GDP,公共事业有公共功能,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黄金比例。可能中国已做得很好,只是具体数据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一个累进的数据,比如说产业税。我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而在私有化层面,我们又希望财富不要太过于集中某几个人手上。所以是累进式。
邵宇:
征税在中国,特别是征遗产税、财产税,难度之大,就跟革命差不多,大家现在都把矛头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绝对的资本跟绝对的财富都会带来问题,最坏的是,财富与权力加在一块。
我觉得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但我非常同意皮凯蒂现在先不征遗产税,等把不动产登记制度搞定了再说的观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本该在今年6月就完成的,现在年底了,还没有完成。征遗产税、财产税,先把家底弄清楚,无论如何都是依法治国。未来一定有一个日程表,大家下一步在一个公正的平台上讨论。那会不会有资本外逃?这是肯定的。法官问劫匪,你为什么打劫银行,因为那里有钱。你为什么资本留在中国,因为这里可以赚钱。该留下的钱还是会留下,哪怕征高额的税也会留下。当然这有一个过程。
如果从全球来看,那可能非常失望,我觉得不大可能征收高额资本税。因为每个国家位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在很辛苦地做原始积累,比如说离岸中心,还有更穷的地方,当然愿意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大家都懂,零税率,三免两减,本来很富的国家,资本就要去资本约束的低地投资。所以,在全球征收高额资本税的操作性是大有疑问的。
刘胜军:
在全球征收资本税我也没有信心,无论是联合国,还是G20,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人的收入不平等,不同国家也不平等,有些国家想利用自己规则上的一些突破来获得一些特殊利益,比如说避税天堂等等,你要想改变这种,除非你有国际强制力,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又建立一种超国家的强制力的希望。
说到中国,其实资本税,遗产税是资本税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死的时候才征,财产税等于活着的时候就征,中国先慢慢来,第一步从遗产开始征,将来如果财富差距还是比较大,可以再考虑。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财产透明度极低,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开征财产税,最终的目标一定落在那些老实人身上。那些有办法的人,都已将财产转移到美国加州去了。
李迅雷:
关于全球征税,我想第一步是不是先在欧洲推行,如果能成功,才有可能在全球推开来。因为我觉得实现社会主义最有可能在欧洲。
在我国,财富透明度确实是个大问题。比如说中小企业,其实有三分之三是不纳税的。
我国的个税改革特别慢,10年前已在谈要征综合税,现在征税还是以在工资中代扣代缴,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征税,没有一个人需要跑到税务局交税。我曾问过财政局的人,为什么不以家庭为单位征收所得税?他说如果这样征的话,根本都征不到税,没有人会跑到税务局去的,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因为我国的财富透明度太低,一些财富数据的比较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意义。在这方面我希望皮凯蒂教授能有更多研究,我想那会对我们的决策有更大影响。想想今天皮凯蒂教授在中国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读者!
另外提一个问题,人口数量对于贫富差距的影响。我就现,在一些人口大国比如美国、印度、中国、印尼,巴西,基尼系数都是在0.4以上,日本在财富平均分配上做得比较好。我有个切实体验,我在公司管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大,一个部门小,每年给这两个部门发奖金,人数多的部门特别好办,距离拉得特别大,人数少的部门奖金就不太好办,因为距离拉得不大。
中国应尽力避免俄罗斯的财富噩梦
托马斯·皮凯蒂:
我并不认为私有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妙招。我认为有不同的互补方式能减少不平等,比如说投资教育比税收更为重要,除非我们需要税收来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我们需要的税收制度是要众人都能接受的,如果中产阶级交税比最富有的人还要高,那就不利于公共服务体系,所以,累进的税率制度很重要。我们还需要渐进的个人所得税,防止不平等的现象达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水平。在没有全球大政府的情况下,在各个国家的层面可以实现这一点。
我们需要更多国际性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比如20国集团这样的架构来确保各国实现财政上的透明,可通过一些国际性条款来实现这一点。
中国如果说出现资本外流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损失。中国如果进入公共的自动信息交流,有关金融资产信息可以自由交流,是非常好的。中国不能像俄罗斯一样,很多俄罗斯寡头跑到伦敦、巴黎,在那些地方尽情享用来自俄罗斯的财富红利,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资产拥有所有权,而这对俄罗斯就像一场噩梦。中国应该尽力避免这种现象。
(上文由本报据陆家嘴读书会暨中信书院大讲堂“从马克思到皮凯蒂:百年资本主义之辨”部分对话整理,标题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