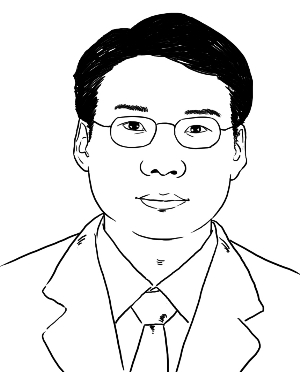|
历史显示,相对于贸易格局的较大变动,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变化要滞后些。全球竞争中的赶超者对其货币国际化,应有完整的认识与足够的耐心,在积极争取参与协调并维护已有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同时,抓住并不断积累可以利用的时机,才是慎重而精明的策略安排。
特定的全球贸易格局,是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根本性经济力量,但不是唯一的。今天,金融市场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秩序的主要支配力量之一。
历史显示,相对于贸易格局的较大变动,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变化要滞后些。伴随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过英国居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贸易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后,纽约并没有同时成为全球金融市场领头羊,时至今日,也不能低估伦敦金融城的影响力。这不仅因为服务于贸易与非贸易需要的金融机制更复杂;还因为全球金融中心连同其依赖的市场基础设施,具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机制特色,是长期逐步聚集积淀的结果,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这套机制一旦被大量使用,就会促成更大量的“羊群效应”式“蜂拥”加入,形成网络外部效应,成为一种自我强化的使用习惯而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其被替代并不容易。
这显示,贸易格局变化在先,金融中心格局变化在后。只有当后者完成变动替代之后,才会促成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调整。
正因为全球金融中心机制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特性,致使在赶超者跃居世界贸易与经济体系首位时,也有搭现有公共机制便车的企图,而不愿付出代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看看二战后美国在要不要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上是多么纠结与不情愿,就会发现那种认为发行国际货币是一种“过高特权”的观念,既没有经济学的有力支持,也没有现实政治实践的强力验证。
1944年至1971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国为全球货币体系守护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为保障的。但是,期间历任美国总统及内阁无不为此大伤脑筋。尼克松的两任财政部长就先后直白道出了白宫的真实想法。先是那位有名而自负的康那利财长,1971年5月月8日在慕尼黑公开宣布美国在国际货币政策上的新单边主义精神,继而失去了与欧洲、日本协调的耐心:“外国人打算压榨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先压榨他们。”更不用说他那句名言:“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继任者乔治·舒尔茨,是货币主义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担任财长伊始,面对企求重建固定汇率机制的欧洲与日本,他大声喊道:美国作为全球货币支付体系看护者的时代已结束了,“圣诞老人已经死了。”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德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各自货币的国际化并不热衷,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抵制。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德国和日本均对资本出入实施管制,限制外国机构进入其本土金融市场,抵制其货币国际化和可能的升值,德国以此来抑制通胀压力,日本则借此为其产业政策拓展空间。
没错,日元是迄今为止跻身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唯一的亚洲国家货币。日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最高年份的1992年曾达15.5%,2012年降至5.7%。但东京对日元国际化并不热情。自60年代受到短期资本流入压力而被迫对外汇体制调整开始,一直断断续续缓慢而非情愿地向前走,直到90年代末才考虑并最后通过消除资本账户限制的实质性措施。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到现在也仍是全球最突出者之一。日本银行研究员田口博雄90年代在其学术论文中明确写道:“最终,日元作为亚洲国家的名义货币锚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趋势,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这种趋势既不应当被鼓励,也不应阻止。”
德、日这种谨慎态度与政策很难说不是明智的。既然还不是全球经济政治火车头,那就不要去企求发挥火车头的作用。既然已有国际货币体系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做个跟随者参与者,能适当分担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尽可能多搭点便车,未尝不是聪明的做法。
当然,从1999年起德国马克已被欧元替代,但欧元的灵魂仍被马克的身影掌控着。马克无疑通过欧元彻底国际化了,这极大地助长了德国外交和政治影响力,但柏林政府也被欧元危机拖进了泥潭。在是否出手救助那些陷入财政和银行危机的欧元区边缘国家事宜上,德国总理在国内反对声与布鲁塞尔欧盟之间左右为难。
德、日对其货币国际化的谨慎乃至抵制态度,不仅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的贸易经济实力仍在美国之后,还在于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远不及美国市场,甚至不及伦敦市场。他们也就不再热衷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而是牢牢把握住自己擅长的实体产业竞争力。
再看看那些追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国家,对其货币的国际化也持慎重态度。新加坡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进其货币自由化,但还是在2000年12月重申新加坡元的非国际化立场。这值得后来者认真思考。
追溯历史发展的脉络,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重大调整,或更具体些说,某一特定货币的国际化,首先是个由市场力量推进的自然选择过程,然后才是国际政治协调过程。后者只能基于前者才可起到应有作用。就市场选择而言,大体上是先私人后官方。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在私人领域的体现,先是用作计价(贸易、金融、大宗商品交易),再是作为兑换媒介的结算支付工具,然后才可能是价值储备的资产价值计量单位。
因此,只有私人选择具备了足够规模与厚度,官方才有介入的必要和基础。官方根据本国私人对某一特定外国货币的选择使用情况,先是拿来作为外汇计价基础,再是用于国际收支融资干预与平衡,最后才可能用作外汇储备。因此,不能一讲特定货币的国际化,就认为直接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货币,是特定货币国际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的关键一步。这一步依赖于该货币能够用于国际贸易、金融、大宗商品交易计价、结算支付工具的长期积累,及其金融市场的配套。
全球范围内的确存在货币竞争,这一竞争过程中的政治推动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力量必须基于私人市场力量才可实现预期效果。这意味着,全球竞争中的赶超者对其货币国际化,应有完整的认识与足够的耐心,在积极争取参与协调并维护已有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同时,抓住并不断积累可以利用的时机,才是慎重而精明的策略安排。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