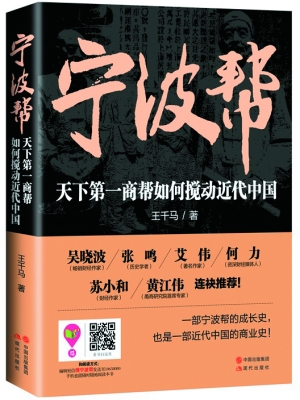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
|
——读《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
⊙吴 歌
宁波濒海。暴怒无常的海洋,使讨海为生者常以生命财产为孤注,和大海赌一把,这是宁波人的性格充满冒险性。恰如梁启超先生所云:“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除了锐意进取、不计得失,海洋赠予宁波人的,还有团结互助的文化基因,因为和风浪搏斗,非一人一力可为。后人在谈及宁波文化时,直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直爽,重乡谊。
王千马在新著《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中,分析了宁波人上述文化特质的成因,“追根溯源,宁波先民大概是古代百越民族北系于越族的旁脉,越地滨江临海,草泽丘陵绵延,山洪潮汐出没于林莽,虫蛇兽类侵袭为害,此外北部还有强吴存在,长时间面临种族覆亡之危。所以,宁波承袭了越文化‘锐兵任死’的峻烈,团体求生的忠诚,也有了九死一生后的自我赏识和自我炫耀,从而演化出几分独特的爽直。宁波式爽直与北方鲁直的区别,就在于不像后者那么个人化、霸道气,而更追求群体共鸣性和认同性,也就更显团队精神。这个从宁波人日常直通通的表白后,往往有‘你讲是呗’的后缀就可见一斑”。王千马进一步指出了海洋文明对宁波人的潜移默化之功:培育了团结、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还有对新事物的敏感性。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士农之后,方才工商。比如,徽州人从商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民逐末利”。直到今天,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村口依旧立有一块大牌子,上面除了写(本村)商者足迹遍布扬州、南京、杭州及沿淮一带,盐商为主,兼营茶、木材、典当等行业……还写有:“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也许,在他们眼里,如果没有朱紫贵,金银山也失去了意义。宁波人因为久处边鄙之乡,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浸染缓慢而且淡薄,在经商的追求上没有包袱,也没多少心理压力。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鄮”命名的县名。此“鄮”即“贸邑”两字合写,意即贸易的地方。据乾道《四明图经》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故有人感叹,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重商的直接结果,是宁波在近代中国搅起的一浪浪波澜。首先,在商业上宁波帮成为中国第一商帮。以钱庄和航运起家,创办上海的第一家交易所,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资金最大、信誉最好的中国保险公司……宁波人掌控了上海、天津乃至全国的商业版图。与晋商、徽商相比,宁波帮更具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经济格局影响因而也最大。其中的商界“牛人”,有创办西药业斗败洋商,并创办上海当时规模最大戏院新新舞台,日后又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有钱业巨子,曾历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会长近15年的秦润卿;有改革药厂创办自有品牌“人造自来血”,曾以小胜大战胜洋货,最后为国捐躯的项松茂;更有把影响扩展到全世界,让宁波帮商业版图变得更为国际化的船王董浩云、包玉刚,有一手缔造香港电影传奇的影视巨头邵逸夫。
其次,宁波帮影响力已走出商界,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北洋混战,再到蒋氏登台,宁波人的身影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中,是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都不得不倚重的力量。在波谲云诡的历史之河里,宁波帮作为一个姿态鲜明、独立自主的政治符号,全程参与和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演进。
在遭遇三千年之大变的时代,徽商、晋商都已没落,何以宁波帮独占鳌头?王千马认为,宁波帮崛起的原因,首先在于较早地具有现代权利意识。他们所结成的现代商会,不仅仅是同乡会,还是公民组织,他们更多使用公权力,而不是依附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无论他们要对付的是西方殖民者,大清朝廷,还是军阀。与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打交道,宁波帮商人拿出了亘古未见的独立性,甚至是决定性,他们以资本为依托,以现代商业体系为后盾,结成了非常强干的一股有实无名的“商业党”,与红顶平起坐,左右着暴力权力的摆动方向。还有,他们在与西人以及西方文明的接触过程中,得以早早地拥抱机器化大生产。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陡然进入工业文明的轨道时,他们如鱼得水,华丽转身,从生意人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家,或者工商兼修。他们大多将自己的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最后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此外,尽管宁波帮擅长钱庄业,但却不像晋商票号那样,死守着自身的一亩三分地而不知变通,相反,他们积极投身银行业的尝试中去,无论银行最终是否杀死了钱庄,他们也在所不惜。正是在这样的姿态下,我们也因此能看见,在很多行业档案中,他们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经济领域也成就了“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匹敌者”的历史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官修的现代史上宁波商人声誉因跟“买办”这个标签紧紧贴在一起而大受损伤。多年来,在名教主义眼中,凡帮助外国人办商业,发洋财的,多半是“汉奸”之流。王千马认为,宁波帮诸位大商人都是传统中国体制格局里的边缘人,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家境贫寒,读书无门。因为边缘,所以才去做所谓“正统”不以为然的洋务。可是这一拨人虽起身于“买办”,但最终都雄心勃勃地做着“卖办”的事业,为中国人的利益在与国外资本打商战,而且斗得你死我活。宁波帮由“买办”到“卖办”的蜕变历程,逐渐形成了中国商人与外商争利、自由竞争的商业格局。这正契合现代商业精神,也印证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
而宁波帮能在洋务、租界、平叛、维新、变法、甲午、庚子、立宪、保路、革命中渗透进巨大的影响,在一个世纪的近代中国连续剧中精彩演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资本开始和传统权力分庭抗礼,商业和政治几不可分,政府对商业有巨大依赖。不像徽商在王朝里做实业,晋商办金融,始终仰仗朝廷的特许经营权,结果朝廷一边利用他们以滋利息、一边以倡优蓄之,随时严密监控、严加防范。宁波商人虽也谙熟政商关系,像严信厚投身李鸿章,虞洽卿也曾紧密追随端方,但他们却在西方势力与本土统治者的较量中找到了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日后,他们甚至以“北袁(袁世凯)南张(张謇)”为向导,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作为新生资产阶级,他们已不满足于自身的政治身份,而不惮于发出这个群体的声音。从“工业救国”,到“教育救国”,再到“立宪救国”,他们改变了商人作为“食利者”的固有形象,也改变了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受贬抑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