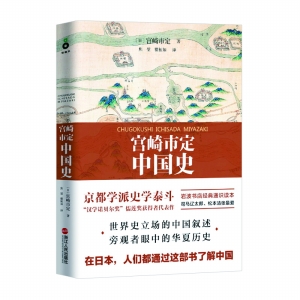|
从经济景气视角探寻历史演进动力
——读《宫崎市定中国史》
⊙林 颐
谈及东邻日本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京都学派确属佼佼者。其中,宫崎市定被称作“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他在中国史学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宫崎市定中国史》是宫崎市定先生积四十余年教学之功,于退休之后受岩波书店邀请而撰写的,初版于1978年。全书分两大部分:总论提纲挈领,通史展开细述。京都学派强调实证研究,注重文献的考订,从中挖掘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宫崎市定在总论中谈到,要借助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坐标轴,整理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这正是京都学派的一脉学风。就本书而言,总论大约占60页,阐发一些学术性的史论观点,通史部分包括了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左右的篇幅,几乎从不引经据典,但原典显然已巧妙地融进了文本阐述,将学术的深厚底蕴化作简浅的语言,成就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国民历史普及读物。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源远流长,怎样耙梳纷杂的史料,勾勒轮廓、建构体系,然后有条不紊地铺排展示,是通史撰写的首要考虑。宫崎市定首先论述了中国史的骨架,即“时代区分法”。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时代区分法”是一种研究常例。划分的标准不同,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梁启超先生当年将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他是以种族的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形态。宫崎市定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宫崎市定的划分方法主要参考了京都学派第一代史学名家内藤湖南的三分法,并结合了其他几位史学家的观点。
对中国读者来说,宫崎市定的四分法与我们熟知的分法有很大差别。原因就在于标准不同。宫崎市定认为,唯物史论必须将经济因素列为最主要的变数,所以他把“经济景气”作为时代划分根据。可是远古时代缺少科学的统计数据,宫崎市定主要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来观察分析。有关秦汉的货币数量,史书多有记载,如《廿二史札记》中就有“汉多黄金”的说法。秦为了收买敌国有权势的人,散掉三十万斤黄金;汉高祖为了离间项羽的属下,用了四万斤黄金;王莽篡位后府中藏有六十万斤黄金。汉代以后,这些黄金却逐渐消失了。中世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不景气”,黄金大量外流到西域等地,国内贫富差距拉大,庄园豪强林立,普通百姓度日维艰。近世是“好景气时代的再来”,商业扩大、流通活跃,庶民阶层逐渐取得话语权。最近世则体现了清末世局剧变而引发的经济凋敝和秩序重建过程。
以“他者”眼光观照“我者”历史,通常在视角上会呈现出一些颇有意思的解读方式,《宫崎市定中国史》显然具备这一特点。近七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的通史研究一向重视政体形态演变,经济状况常作为侧面补充,但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宫崎市定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经济演进的脉络上,尤其是货币信用对国家凝聚力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想来会对我国的史家有所启发。我国的二十四史,除了太史公的《史记》,对经济少有记载,国史研究由此被诟病为“帝王家史”或者“英雄史”,宫崎市定摆脱了这种僵化的研究模式,在他看来,“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对帝王政绩的过誉,这些所谓明君只不过时机凑巧,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口缺少也无失业之虞,因而得以人人安居乐业。基于中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个人的影响力有时候确实可以改变事件的进程,宫崎市定对此一概而论之是欠妥当的,不过,换种眼光,我们能从中可以看到他研究历史的平民化视角。
宫崎市定对“农民起义”的说法表示质疑,他认为历次起义领导者大多是地主包括工商阶层,而参与主体很多是失业的手工业者。改朝换代于普通民众并无太大感触,经济活动却往往和百姓日常息息相关,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状况,也可以看成是经济需求创造了国家复合的契机。宫崎市定还不时将中国与同时期的日本、欧洲的发展做各种比较,令人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史学功能的变化,从经济角度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当然,“他者”的立场有时也会暴露出一些隔阂。最主要的问题,笔者以为是对引起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阐述不足。许倬云先生85岁出版《说中国》,他的想法是“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变动,常常是很多条件共同构成变量,经济因素反而是跟着其他条件在转的。例如在马克斯·韦伯有关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思想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如果说经济推动了历史,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经济?另外,从经济学研究角度,关于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的历史记载,是否比起货币量的变化,更能标识经济景气的程度?
阅罢全书,回头细想总论中关于“信息与选择”、“历史与记忆”、“方法的选择”等相关论述,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从事实中抽取材料、构建合乎逻辑、发人深省的史学理论呢?宫崎市定的“时代区分法”与梁启超的研究方法有极大差异,但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开辟广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去观察研究。所以,虽然宫崎市定的这部中国史问世快四十年了,梁任公的著述距今九十多年了,却仍常读常新。他们的求索,让我们对史家职责、史学精神,有了更明晰、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