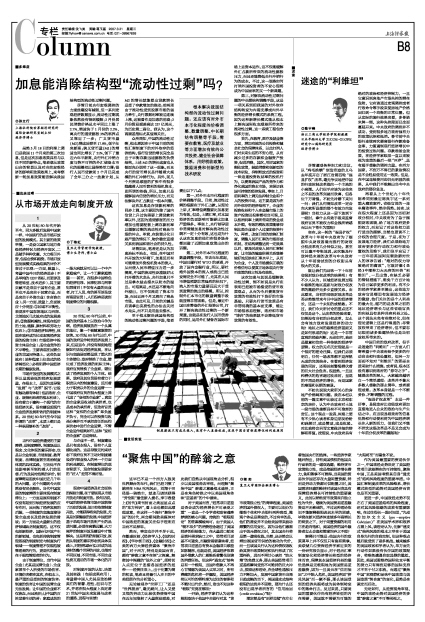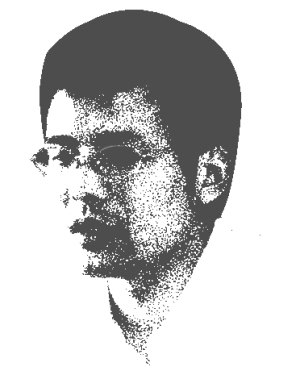|
实在,这一轮的“强县扩权”改革与十年前中央政府为了摆脱中央财政困境而推行的财政分权改革有几分神似之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触及行政神经末端的改革与中央政府从十年前尝试到的分权甜头有很大的关系。
就让我们先回味一下十年前省级财政分权改革的结果吧!有不少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悬殊的地区差距与财政分权改革的激励并无多少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当初的省级财政改革是否必然能带来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一个未知的或然数。不过,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重点还不仅仅是这个。从改革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当初的分权改革,怎么会有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呢?地区之间的悬殊经济差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经验判断。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相信前一种传统的经济学逻辑。权力的无名氏定理就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注脚。但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一场改革都不是浑然天成的完美结合。在看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时刻警惕潜伏着的巨大社会危害。很显然,一旦这种潜伏的危害超过收益时,呈现的不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国家的崩塌和长期的衰退。
不妨先说说大家所关心的房地产价格畸高问题。我在本栏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比较过北京和东京的房价,认为中央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观点一发表,网络上便有不少热心读者和身边朋友纷纷和我探讨,或是赞成,或是批驳。对此我将会另写文章做详细的辩解和答复。按理说,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力,一旦它意识到房地产市场失控的潜在危险,它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或者行政命令等手段来使房地产价格回归到一个均衡的正常位置。但从实际的施行效果来看,多骨诺米牌一倒,这种失控局面已全面蔓延开来。中央政府的调控并不成功,受到很多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抗拒和抵消。春节前中央银行连续两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力图遏制现行经济增长中的投资过热问题。存款准备金政策,在经济学家眼里一直以来被视为政策的最后一把“巨斧”,具有超乎想象的调控力量。在西方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会轻易使用这一政策。但是,在中国连续使用却仍无明显的效果,从中我们不难解出当今中央政府的那份急迫。
再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希同到最近陈良宇这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省级官员的一连串腐败事件,绝非偶然。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当初财政分权时,中央政府为了急于摆脱财政困境,给了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而忘记了对这些权力进行适当的捆绑,当然也更谈不上分权的合理尺度。于是,在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我们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行动权力和行政处置权的思维下,我们似乎忘记了一百年前英国阿克顿勋爵对世人的谆谆告诫:“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它就好像《圣经》中那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利维坦”,一旦出笼,在缺乏必要的管制措施下,难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有不少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哪里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他们关注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碰巧的是改革之初的地区经济增长与这些省级官员的利益具有某种共容利益之处。这个说法未免有些绝对化,但在理论逻辑上还是行得通的:尽管放权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不要忘记眼前诸多难题恰恰也是当初放权所带来的。
中国目前的政府改革,似乎是迷途的“利维坦”:一方面人们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给予更多的行动自由和行政处置权,但另一方面却不知对“利维坦”的邪恶本质采取什么措施。或者说,根本还没有意识到政府的“掠夺之手”。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家越来越明白一个简单道理:改革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顺理成章。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妥协、不断调整的过程。
“强县扩权改革”本是一件好事,县级政府比省级政府更加直接地进入公众的政治与生产生活之中,应当说县级政府的信息优势和行动便利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我们又不能不担忧这场改革是不是又会成为十年前分权改革的翻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