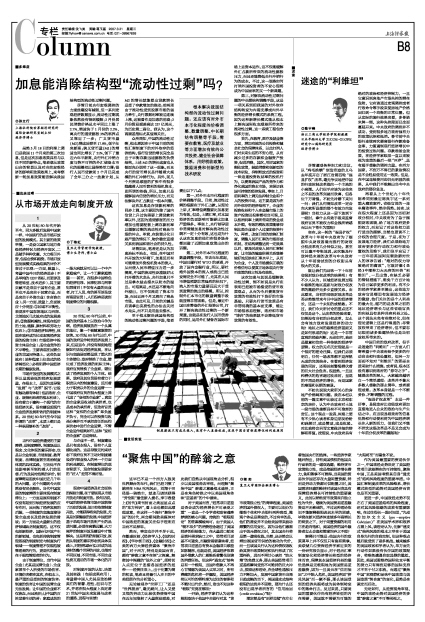|
然而,事实也许并不尽于此。在敏感时刻,《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之类的西方大牌经济媒体“聚焦中国”,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深意。解密其中深藏的“弦外之音”,须将切入点定位于连接各国经济的纽带———经贸往来上。出于化繁为简的初衷,笔者且将最引人注目的中美经贸作为分析重心。
无论被视作“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厨房”,毫无疑问,让人又爱又恨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在近年间堆积了大量贸易顺差,对此我们自然从中国视角去分析,很少以美国视角去审视。而理解“聚焦中国”醉翁之意最根本途径,正是在角色转换之中以美国视角体味“逆差者”的个中滋味。
对于美国而言,“经常项目逆差是否会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承受之重”一直是一个令学者和政客魂牵梦绕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极限理论”的答案模棱两可:由于美国人“朝不思夕”的消费理念超过了美国经济的供给能力,在大量进口舶来品填补需求缺口之中,经常项目逆差不可避免,而融资需要意味着,经常项目逆差总有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如影随形。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依靠国外借款人的仁慈维系着繁花似锦的消费狂热。但这种“透支式”结构总有一个极限,当国外借款人不再心甘情愿为美国人买单之时,所有潜藏的危机将一并爆发,美国经济将以可怕的牺牲率为过往的奢侈和不羁付出代价。然而,谁也不知这种“极限”究竟在哪里?
一开始,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极限取决于他国中央银行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青睐程度。美国经济的国外债权人,主要可以划分为微观个体和中央银行两种类型,微观个体总是善变的,不过有幸的是,他们的善变并不会给美国带来波动频繁的信用变化,因为当他们意图出手美元债权之时,其本国央行将是第一道吸收线。当然,这必然会以增加该国货币供给的被动为代价,而一旦该国央行认为这种债权吸收给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形成了沉重桎梏,进而不再甘心承担“防火墙”的免费义务,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瞬间受到不可维持的巨大冲击。按照这种理论,在全球性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货币当局日趋成熟的当下,美国透支式结构极限的达到并不困难,那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学者所言的“信用抽回(credit revulsion)”呢?
那定然是有“别样思绪”在左右着他国央行的选择。一些经济学家随后指出,持有美国债权的他国央行面临的是一道双选题: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或是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美国的贸易伙伴国还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可供配置之时,美国需求旺盛的维持对该国而言具有保障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此时以牺牲货币政策些许独立性为代价,继续为美国贸易逆差融资是不无裨益的。不过这种理论依旧不能解释极限迟迟未至的困惑,毕竟在新兴经济体连续多年高增长的背景之下,对于闲置资源的利用正在趋向饱和,美国经济的国外融资者怎么会鱼和熊掌均弃之不理?
解释只可能是:他国央行的政策菜单上并不仅仅只有鱼和熊掌。美联储几位资深经济学家近来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对于经历汇率制度变化和经济增长转型的经济体而言,保障其本国经济利益的最优选择是无极限地为美国贸易逆差融资,因为一旦美元在“信用抽回”之中陷入危机,美国经济因“挤兑风波”而一蹶不振,那么该国受到的经济共振将成为其体制转变中的致命打击。反过来说,只要美国的重要伙伴尚有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美国就不需要为可能的“大限将至”而寝食不安。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政经走势决定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潜在的可持续性,聚焦中国,正是美国考察其自身“透支式”结构风险程度的重要举措。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风险维系、增长模式转型的趋势对美国经济而言也是至关重要。
更进一步,中国政经走势不仅左右了美国逆差结构的风险程度,还对其风险规避的成败有重要影响。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先动的加尔文主义(pre-emptive Calvinism)”在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占据上风,该理论认为,化解“透支式”结构风险的根本之举在于美国自身先行的自我克制。但这种观点随后就受到了诸多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和学者认为,单方面先行动作如果没有伙伴国的政策配合,将难免遭遇自取其辱的尴尬。因此,美国试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努力只有得到足够的国际支持才不至于付之东流。而通过“聚焦中国”来观察和品味中国政策与美国政策“契合度”的变化,显然是在谋定而后动。
无论如何,从经贸视角审视,中国的政经走势对美国经济的多重“醉翁之意”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