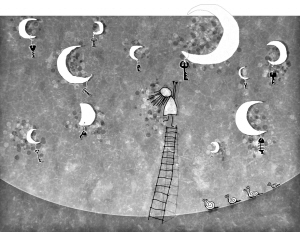|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文人”不需要产权、物权。俄国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言“我只需要一把牙刷”,但即使如此,斯大林还是很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士可投靠君主或贵族,享受俸禄或禄田;可以当食客门徒,可以纵横捭阖。实在不济,士还可“下海经商”,子贡、范蠡都是大商人。但士不敢投靠企业家,更不敢当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的身家性命没有保障。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物权的本质是允许、保障人们使用和享受其劳动成果。广而言之,以物权为基础的财产权利制度,是一套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近世以来,面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些人看到了它的科学技术,一些人看到了它的坚船利炮,一些人看到了它的廉价商品,一些人看到了它的自由民主……这些见解不无道理,但更深刻、更基本的缘由却是,启蒙运动后数百年来的欧洲,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且连贯的关于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思想体系及法律制度。
168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论政府》中提出: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1794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理论与实践》中说:所有天性理智的人们对法律的可能赞同,是考量权利合法性普遍适用的尺度。1985年,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德·雅赛在《国家》中论证:国家通过再分配来“搅和”福利,要比真正下功夫创造福利花费更大的精力。政治家们所设置的“激励机制”在长期可能会对福利和自由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尤其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平民财产也开始受到保护,哪怕是一间茅屋,未经许可,也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而数百年来的中国在做些什么呢?“元跨革囊”后,人即分为四等,遑论财产!明以降,朱元璋们不遗余力地剿杀社会财富,拼命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豪强们借机剥夺乡民、兼并田亩(金庸小说里描写一个逃亡者,一夜狂奔也未能逃出那个恶霸的地面)。清以来的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举国体制”下皇权社会的回光返照,及至清末要搞什么“宪政改革”,那已顶多是一剂强心针罢了。命运多舛的民国,内外交困,民不聊生,注定了“三民主义”是朵好看却短命的昙花。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落伍和挨打,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人民赖以为生的基本财产权益被剥夺殆尽。
现在好了。经过几十年的挫折,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物权法》。虽然还粗糙、不完善,还多少有些滞后,但这毕竟是迈向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起点,是中国经济社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物权的根基在地权。有了《物权法》,人们就可脚踏实地;而能够脚踏实地,人们就有了生存的根基和稳定的发展。
远的不说。从近期看,倘若没有《物权法》,中国就无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贪官污吏假公之名行掠夺公产、私产之实的问题,还有“失地农民”问题,“钉子户”问题,“访民”问题,就会愈演愈烈,离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追求将渐行渐远。我们经常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莫过于其最基本的物质财产权益。所以,一旦落实了《物权法》,也就意味着落实了最基本的人权。
回顾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史,中国人在物质财产的权力和权益问题上不啻兜了一个大圆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一大二公”,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再到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及至二十一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非国有经济、非公有经济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平民百姓的生活也因此逐步告别短缺、匮乏和贫困,开始步入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小康之路。由此可见物质、物权的力量有多大!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中国十五年前就已经确立了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抉择,那末就不能不明确产权,就不能没有《物权法》。《物权法》在经济社会制度的意义上对公民私有财产的肯定和保护,不仅彻底扬弃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教条桎梏,而且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此,中国人或可真正一心一意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