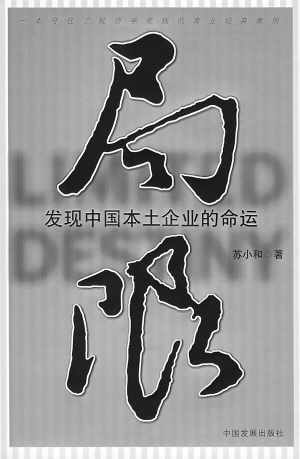|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每段历史的不可逆转性以及不甘于平庸的自我期许都促使每个时代的人深信站在独一无二的风口浪尖,身处不好不坏的年代好像平淡得可耻。或许,这只是个试验的年代?至少,苏小和这样认为。
恍然,已是检点30年改革的时候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民营企业的出现对于制度变革的推动力量无可否认,一群原本微乎其微的人物改写了历史;时过境迁,今资本已成最大的母题,为企业家立传为公司立史在当下似乎有了为生民代言立命的紧迫感,因为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相对自如地来完成对历史的诠释。
于是乎,在丰富的管理案例中,在繁多的财经特稿中,在嘈杂的商业评论里,人们读到了一个又一个以雷同的话语系统完成的企业宏大叙事:一个小人物,心比天高,顺天时争地利,搭改革之春风,乘经济之快车,万千惊心动魄之后一个华丽转身,修得正果,或许在此之后,还应该加上国际战略,资本市场,企业慈善,公司责任等等时髦词汇。幸运的是,毕竟还有人在坚持洞察“光荣与梦想”背后的局限与乏力。
苏小和关于民营企业的话题触角,最早由对多元化神话的解构开始。从2000年以后,迈克尔·波特代替德鲁克成为企业偶像,不少管理论坛频频向波特致敬。这位全球竞争力之父的教义其实也相当简明:在美国,非相关行业购并的转卖率高于70%,这说明大部分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失败的,企业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差异化与专业化。只是无论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波特的讲座上表现得多么热情虔诚,在现实中仍在尽可能地扩张,要将多元化进行到底。
为何波特的理论在中国变味、失效?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国内不少学者以及企业家找到了多元化的典范———GE的杰克·韦尔奇。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战略之争,但在中国语境下,远非那么简单。复制过来的战略术语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匹配,只能是奢侈的空中楼阁,或者,我们根本就缺乏谈论现代企业的元制度环境。在公权利难以制约的环境下,私有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民营企业的处境首先是谋求生存空间,短期投机行为因此最有激励,而所谓的多元化游戏只是简单的堆积,路径总是尽可能地多进入厚利产业,谋求快钱。而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所谓的企业战略,只能是异邦的想像。如果能够明白这点,也就能明白苏小和逻辑的起点:一个大政府背景下的民企生存状态只能是妥协而扭曲的。
《局限》立意在于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或者本土文化的商业模式研究,但是视角却游离于主流话语内外。书中,国际管理理论失效,企业宏大叙事终结,甚至出现的企业家,也大多很虚弱:穆军因对潜规则的默许付出十年维权代价;唐万新的梦想永远无法照进不宽容的现实;魏文彬无法推行一个简单明了的动议;孙成钢陷入了自身的悲剧中无可奈何……作者调查了相当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它们的商业模式惊人雷同。中国人复制的能力真是太强了,这注定了中国企业的普遍短命,同时也使得本书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保持相当的冷峻。
眼下,乐观的理由比比皆是,而悲观则更需要立场,苏小和引了一句别人的话“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100年前的英国”来表明他的立场。对于东方企业文化生态的弊端,他有显然着更为具体的理解:那种所谓的感情式管理后果难测,中国式的聪明往往导致管理缺陷,企业领导决策随意性带来决策的低效率,企业家缺乏管理素质,国企民主过度,而民企独裁成性。语虽偏激,却亦占其理,几千年的人治积淀让国人几乎本能地以道德代替规则,现代性的阳光普照毕竟来得太晚,商业文明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必须要像搞政治一样搞企业”,“在中国,不懂政治是搞不好企业的。”……中国企业泛政治化的倾向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狂热,大多数企业家的说教常常是以这样开始,苏小和甚至以为《水煮三国》的流行揭示了国人常识的错误,以规模来谈论划分企业,而不是产权。阿玛蒂亚·森一再强调应该把自由作为发展最重要的标准,可是在私人产权没有明晰划定的情况下,一切规则难免暧昧,即使短期内可以超常发展,但是制度缺失的阴霾却使未来难以预测。
苏小和的工作本身亦带有试验性质,他或许道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普遍困境,但要论解决思路,却已经超越这一代人的能力,也许,这就是试验的局限,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