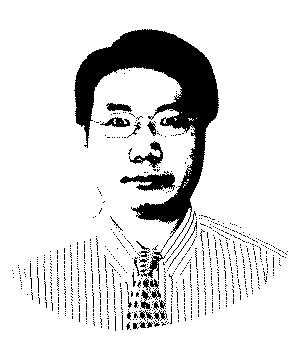|
宏观经济政策应 “一视同仁”,其最终目的必须是为了全体国民的福利保护与增进,而部门分割与利益封闭化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确定及有效性。某种程度上讲,中央只是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执行力,地方则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执行力越有效,宏观政策对国民福利的负效用越大。
罗贯中《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准确概括了中国二千多年漫长专制社会的政治格局变迁特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阻挡不了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而每次都有中央与地方关系恶化的影子。到了民国,更呈地方割据的“军阀混战”态势。由此,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而保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领导权,便沉淀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条基本理念与原则。顺理成章, 1949年之后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建设与历次改革,学界与实践界都将精力集中在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体制上,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央政府各“部门”及相互间协调机制的建设与改进。
然而,改革走到今天,如何协调与掌控“内阁”各“部门”,使之形成维护与增进国民利益的合力,革除“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小团体与个人化”以及“小团体与个人利益法制化”的怪状,越来越成为急待研究并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了。
我在本专栏多次提到并强调,宏观经济政策应是“一视同仁”的公开公正的“国民经济政策”,其最终目的必须是为全体国民的福利保护与增进服务,而部门分割与利益封闭化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确定及其有效性。某种程度上讲,中央只是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执行力,地方则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执行力越有效,宏观政策对国民福利的负效用反而越大。
涉及经济管理的中央政府部门,无论是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还是行业监管机构,无一不在片面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或者只看到一个方面的重要性,总强调维护与增进所负责管理的特定领域利益,阻碍公平竞争,大大降低了行业或市场发展效率。对此,有太多的事例可予佐证。
为什么理应早就出台的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有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合并的法案一拖再拖,好不容易通过的法案还留有“尾巴”?为什么直接涉及民众利益的电信、电力、邮政、能源等行业的竞争格局推进远不如人意?为什么迟迟形成不了有力有效的环保政策?为什么金融行业的改革与效率令人担扰?就连公司债券管理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不总有“部门”的因素吗?
我想在此特别提一提“利用”或“吸收”外资的激烈争论。最近有商务部官员公开宣称“并购应该说也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不否认并购是吸收外资的选择,但绝不同意“是必然选择”。翻翻经济史,当一国经济增长处于快速增长轨道时,多为本土资本“走出去”并购境外资产,极少有大量外资并购本土企业;只有当一国经济下滑之时,外资并购可能增多。而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全球范围内基本预期一致的事,处在这样的增长与发展阶段,怎么“并购是吸收外资的一个必然选择”呢?外商到中国投资,有多种形式与渠道,并购也只是其中之一却远非是必需的形式。允许本土企业与资产被外商并购,理应最为慎重、最不常用。要不然,会远离“国民经济政策”的原则,而更多体现出“外商经济政策”的色彩。
遗憾的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实政策就是这种观点指导的产物。有些官员在反驳社会各界有关外资并购会形成外商垄断并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的越来越强大的呼吁时,总拿以下两点来支撑来辩解:一是,“2006年(外资)并购活动金额仅仅是47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数的2.5%,数量有限,而在专业制造业领域只占1.7%”;二是,“监管当局”对外资并购能否形成垄断是“非常关注的”,尤其是针对外资已经在一些行业占有较大比重而形成事实垄断的现象,“监管层对于某种形式的垄断采取了豁免的形式”。我认为,无论是从经济分析还是现实情况看,这两个理由都显得软弱无力。
观察外资有没有控制本土的重点核心企业与行业,并不是从其投入并购中的资金多少而言的。其实,外资已控制了部分核心重点骨干企业与行业,这连负责这一领域监管的商务部官员都承认,否则,为什么要“对于某种形式的垄断采取了豁免的形式”呢。在这种情况下,外商投入资金越少,只能说明其并购成本小。完全可以说,2006年“吸收”的那“47亿美元”的代价太大了,完全偏离了真正的市场交易价值。这当然主要是包括“部门”与地方政府在内的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的结果。
再者,中国今天尚无《反垄断法》,作为行政力量的“监管层”如何把握与识别哪些外资并购不涉及到产业安全?有什么权力对“某种形式的垄断”采取“豁免权”?“某种形式”是什么样的形式?由谁通过什么程序来界定?这“豁免权”又是如何界定并由谁赋予的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之前,所谓“监管层”的政策也仅仅是“部门政策”而已,其随意性以及其中的诸多弊端,或许某些外商的感叹袒露得最清楚:中国的事说难做也难做,说好做也好做,只要将行政机构打通了,就是一路绿灯。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不确定最脆弱进而最易受损的,就是国民福利了。
如何防止与减少国民利益分割与部门利益膨胀,并尽量使部门政策真正体现出“国民政策”的合力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在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重视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同时,从思想意识上也应重视中央政府各部门关系的协调与治理问题,尽快打破“部门思维意识”指导下的政策确定机制,形成并不断强化中央政府层次的“一统化”的“内阁”理念。二,从根本上形成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政治建设格局,尤其是增强“人代会”的建设及其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制约力度。
前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讲过,他在担任日本央行行长期间,被国会质询是家常便饭,最多一年曾达80多次。试问,我们的央行行长与部长们,一年被“人代会”“质询”过几次?看看每年美国总统在国会作的“国情咨询”与财政预算报告长达多少页,再瞧瞧我们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与“国家财政预算报告”又是多少内容,又能具体到何种程度,对“人大代表”与公众又能披露多少信息,就可以明白,“内阁改革”与政府监督机制建设是多么任重而道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