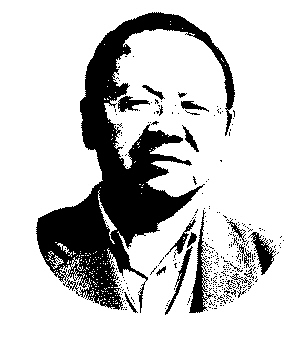|
只有有效的制度供给,才有真正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机制”。
一切生产、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都是人类与自然交织的活动;欲使这些活动产生人们所预期的成果,就必须对这些活动进行组织和协调,以便有效管理和治理。为此,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以及行为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制度的功能,是给处于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提供相互影响的框架,通过它,人们由以确立各自的选择“集合”,进而在这种“集合”中达成一种竞争———合作关系。制度的宗旨,是“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只能经由制度去均衡、协调不同当事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古训“无依规矩不成方圆”,就包含有制度的意思。
比如交易———一般的,人们都有通过交易获利的动机———设若有种制度,可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使彼此都能承担、履行成交后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则这种交易就可长期持续并扩展下去,人们也就能够长期地从中获益,或者说实现各自的比较利益,并增进社会福利。这就是良法良制。反之,若既有的制度并不能规范交易当事人的行为甚至扭曲了交易,则不受约束的“私欲”就必然导致“一锤子买卖”、“短期行为”、“呵哄吓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无序现象;这样,交易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遑论扩展!这就是莠法莠制。莠法莠制与“诚信”的缺失是相对应的。
由此也可以说,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信用危机,除了“道德风险”,市场制度的缺失或畸变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简单地说,社会经济需要管理,企业公司需要治理,“大事务”的管理和治理需要“大制度”(Regimen),“小事务”的管理和治理需要“小制度”(Institution);前者譬如计划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后者譬如统收统支制度或独立核算制度。暂且撇开技术创新的意义不谈。不言而喻,管理效率的高低、治理效能的优劣,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如何,而制度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制度的形成机制和变迁机制。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素有“理-法-权-术-势”的脉络,今天人们所谓的制度,有“官”即有“管”,有“管”即有“治”;无论大小事务,都重在一个“理”:“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礼记·乐记》)可讲“理”不容易。用现在的话说,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以但凡为管为治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理”需要讲需要喻、以便让人们知晓认同接受的“道理”,而独对“法-权-术-势”领会有加发挥有致。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以理服人的事也就不常有。怎么办?约束人众还得有法,“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但“法”有滞后和“法不责众”甚至“枉法”的时候;于是就有了“权”的介入,以力服人的事因此不绝于耳。不过,纵使一声号令莫不从命,实也免不了“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这时“术”就派上了用场,来一个朝三暮四或声东击西或望梅止渴或分而治之,也能对付一阵子;再不济,还有“势”可借,拜内力所赐或假道外功,效果常常也会出人意料。故官箴曰:“理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有权;权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有势。”
但话又说回来。为政为官或为厂长经理CEO者,总会有理屈词穷之时,总会有不可理喻之时,且一旦遭遇“法无定法”,“计划不如变化快”,就必然逼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回应(“政策”和“计划”不足为法,盖因其无常态且往往自相矛盾,所以可预期或可预见性差)。进一步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者管理者也有滥用职权的时候:在一言九鼎之下,大家虽然会跟着“家长”的“指挥棒”转,但大家也会向“家长”学习,“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荀子·君道》)这样一来,管理层和组织内部就必然黑暗、混乱和腐败。而“术”是藏在“你”心里暗自运用的,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援法入儒”,管理上就是“授意”的技巧,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滥玩“术治”,难免会搞得人人自保,人人自危,实在不可取。多年营造而成的威严名望,就是“势”,“气焰也。”(《增韵》)尽管已经无法可依、无权可用、无术可玩了,但还有“老本”———只消挥舞起某杆大旗,营造出某种氛围,“态度决定一切”就能吓得人噤若寒蝉,但弄得不好,就成了孤家寡人。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辞,破绽百出……这时就被动了。一旦“势不足以治”,结果便难以为继。所以,若真的还要想发展,就非得把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放在首位不可。
就像人们离不开清新空气、洁净活水一样,经济要想有效增长,社会要想和谐发展,就特别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有效的制度供给,才是真正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机制”。问题是:有效的制度供给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