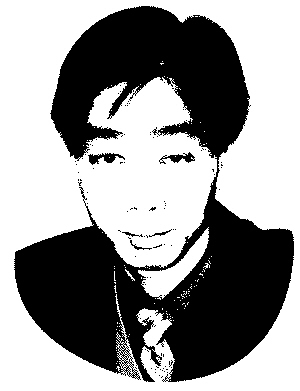|
确实,商业管理体系的确是一道横亘在国内企业发展过程的“天然”壁垒,至少是让很多人感到困扰的心理障碍。但是,由此而探究所谓中国式管理,笔者大有怀疑。
首先,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专业是由德鲁克等人奠定的,如果我们的对话框架并没有也不能跳出西方式管理所设定的三大对象、两大职能、八大目标等,那么,我们所能做到的顶多也就是像日本那样创造出两门半管理方法,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不过是在西方式管理框架内拾遗补缺而已。如果想重起炉灶,要么我们所创造出全新的商业管理理论体系,与现代那个叫管理学的东西完全不同;要么,国内的企业在管理架构、运作等方面别创一种管理制度。这似乎不太可能。
其次,很多人,甚至包括像北大何志毅教授那样,认为中国人不乏创造力,没有西方理论照样造出了原子弹,甚至猜想中国式管理会在2028年左右形成。但问题是:一,中国原子弹与西方原子弹在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最多不过是中间的函数变量或方程解法不同,殊途同归罢了,否则两者就不能统称为原子弹;二,如果中国能够及早获得西方原子弹技术,试验岂不可以提前成功?三,中国式管理在2028年左右形成的种种提法,不免让人觉得避重就轻。究竟中国式管理外延有多大,至少要让人们看到中国式管理外延的边界吧。如果可以无限延伸,那就没必要提什么中国式管理了。中国式管理究竟是要“贴地飞行”,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炼丹炉而形成,还是要根据现行的国际通行管理理论和模式展开?
相对于种种见物不见人的提法而言,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显然要充实许多,曾先生的想法是根据国内各区域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探讨。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一边仍然是在西方式管理的框架内对话、创造,一边提出“中国式管理”,那么,终有一天,甚至会形成北京式管理、上海式管理、广东式管理,随着外延的不断扩展,其内涵也必然趋近于零;退而求其次,在市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伴随着管理理论及模式的差异,贸易冲突恐怕也会越来越严重。
曾先生主张,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来实现管理的有效性。他说,“研究中国管理哲学,必须对历代先圣先贤,抱持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辛勤耕耘,便没有今日丰硕的成果。也要对列祖列宗表示虔诚的谢忱,没有他们的用心传承,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宝贵经验。”如此,则要看这种管理是不是真的有效,合不合理。国内企业在组织行为、消费行为、变革对象、模式等方面,的确大不同于西方企业,有效性的提法倒是颇符合管理的动态性本质。但是,如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便意味着迅速兴起的读经运动、复古主张,我不免抱以深深的不安。
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除了诸子百家时代以外,长久处于缺乏思辨的状态,类似于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几无可见,而与之相随的,则是盲目的崇尚、莫名其妙的敬畏,这使国人在少不更事时便丢失了自我,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特征,这可说是当今企业文化的通病。商业实践中的暴利性诱惑,以及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人权利缺乏尊重(极端的例子是近期的山西黑砖窑案件),迫切需要我们打破不合理传统、寻求商业管理体系的合理性、规范性根据。如果再将这种失去主体性特征的哲学强化到企业管理中,我认为,不啻于一场灾难。
事实上,以当前的国内企业管理现状,我想,可能更应着力于两方面的思考:其一,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管理实践尚不满30年,商业理论几无积淀,也就是说,国内企业与西方企业主要还在于阶段性差别,还需要向现代科学管理模式迈进,正如福特公司从老福特时代向福特二世时代转轨一般;其二,企业管理归根结蒂是人的管理,而中国话语中的人与西方话语中的人,其主体性地位大有分别,因而,企业管理理论的变革,恐怕还需要进一步上溯到关于人本身的探讨。但这已经不是管理学能兜得住的了。
总之,我认为,如果将中国式管理限于方法论层面,就像当初日本创造出二门半学科一样,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将传统认识论强加于商业管理体系,甚至仅仅因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那么,很可能就像《等待戈多》一样,等来的只是一场虚无,更要命的,会贻害企业、社会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