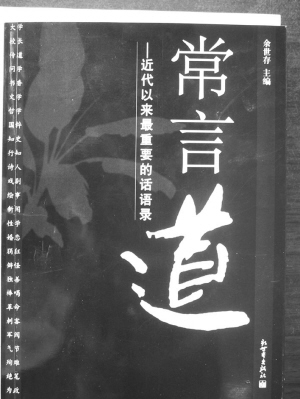|
前年,余世存先生推出《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今年,余世存先生再推出《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两书堪称姊妹篇,都是通过搜罗历史上的细节,以历史上的人事、人言,来揭示人性、管窥历史。
《常言道》封面有句话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最重要的人,最有价值的话语,近代史所散落的珍珠,全都串联在了本书之中。”这也许是出版社的包装之言,因为,说本书是“散落的珍珠”,固然不错,但若说有什么“串联”,笔者以为,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读者,如果读者有心,能看出名堂,那就能把书中搜罗的“珍珠”“串联”起来。
书中《二十五:爱国》一节是这样讲的:1948年,伪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当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
中国官府自古以来都是高深莫测,只有进入它的高层里层,才有可能看清它到底几斤几两,然而可哀的是,一旦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却又往往叫人大失所望、悲从中来。当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正统儒家济世思想踏入仕途,然而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兴趣全无,晚年只以卖药谋生。海瑞也是类似的命运,他有儒家兼济之志,可他做一县之父母官,平日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他说:“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诵,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他还发牢骚:“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海大人不甘心干迎来送往的勾当,当今的公仆干这些却似乎心安理得,不是有公仆大言不惭地说吗,接待也是生产力!杜甫不能济世,即去救人,海瑞不能济世,就辞职不干,去独善其身,当今的公仆倒好,处心积虑杜撰一些歪理邪说,欺蒙世人,真是恬不知耻。
书中《二十六 狷狂》讲的是文史大师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一贯婉拒新闻界采访,也拒做寿搞Party,也不参加什么会议,他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钱先生眼光端的是犀利无比,他把世事看得太透了。会议是公共活动,是政治伴生物,但许多会议确实叫人不敢恭维。有人这样描述概括机关里的会议:“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不言不语,五六七八九把手,只做笔记不开口。”手中有无真理,以及真理多少、话语权大小,完全取决于手中是否有权力,以及权力的大小。还有人这样说今天的会议:“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开会几乎沦为表演。还有人调侃,说只要会举手、会拍手就可以参加什么会议。
书中《二十九 气度》讲民国旧事。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大头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下以为,近代中国政治比之古代中国政治进步的地方,在于近代玩政治的人比古代玩政治的人少撒了一句谎,古代政治人物在做政治宣传的时候,总是先自称自己代表天意,其次才自吹自己代表民心,近代政治人物则不同,近代政治人物删繁就简,只称自己代表民心。袁大总统和蔡先生是在一条河里洗澡,彼此都深知对方,他们如果太罗嗦,只能叫人认为太无聊。可叹的是,人随王法草随风,近代影响到了现代,自吹代表的歪风影响所及,社会各阶层无不深受其荼毒,比如有时候你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电视节目,冷不丁地,从天而降的节目主持人会说:我代表全国电视观众向你问个问题,或云我代表亿万观众向你表示感谢。代表,代表,代表,谁知道你代表了什么,代表,代表,有多少罔顾民意的东西假汝之名大行其道?
手捧《常言道》,边读边想,思接书里书外,视通近代当代,不禁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