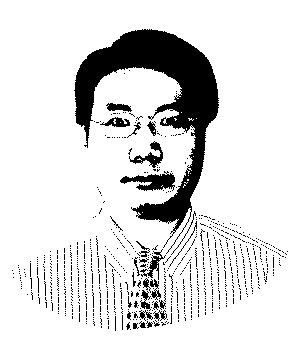|
与传统权威不同,权限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处处存在着的。所谓权限,自然意味着不管什么权力(利)都受到有效制约,有确定的边。这个边界,或者由法律规定,或者由道德约定。对此,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
如果说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还有权威,那也是一种由某一范围的社会主体所心悦诚服予以承认的权威。这恰恰是以现代市民社会所认可的权限为全部内容,而且其中权限的行使必须为民众带来某种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利益。因而,现代社会里的权威也就是民众认可并敬重的权限,任何希望通过强制性力量树立的权威都不可能成其为权威。那种认为行使不受约束、没有边界的权力(利)就自然会得到并占有某种权威,简直就是自以为是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
在西方社会的中世纪时代,人们生活在由宗教———教会的“神学权威”以及国王———封建主的“世俗权威”所支配的世界里,不平等与隶属关系原则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原则。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交换领域不断得到突破,“等价交换”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日渐向私人领域得到重视与保护的流动化与分散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市民主体”、“市民社会”逐步得以确立,社会从原来的宗法等级结构进入到至少在倾向上须相互平等对待的“市民交换社会”,原来那种不平等与隶属关系原则的根基自然就越来越受到威胁和动摇。
在此基础上,思想启蒙运动从康德启始,高扬“理性”旗帜,在精神领域公开批判宗教———教会权威,加之这种传统权威也不具备可由理性计算的即时“交换价值”,从而使“神学权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败退、萎缩。
但思想启蒙运动并未就此停步,随着科技进步与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启蒙思想者们将“工具理性”不断运用到新的水平。在彻底打垮“神学权威”之后,也对以“王权”为特征的“世俗权威”予以强烈批判,这不能不说是导致“世俗权威”最终衰落并促成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现代权限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以至于当今之世,不管是神学还是世俗领域,只能存在由权限构成的权威,没有了那种天生的或不受制约而无所不在的权威。即便是这种权威,那也得必须向社会证明其本身首先具有某种功能性,并具有权限性。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权威批判在打掉传统神学与世俗权威的同时,最终却自觉不自觉地确立了“工具理性至上”的新权威,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被冷漠运算并可予以利害权衡的东西才有价值。这种新权威最集中地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利用与控制上,甚至忘掉了思想启蒙者最初确立的“权限原则”,越来越演变为“人定胜天”的蛮横,肆意掠夺大自然成了下意识的常性。
这足以证明,对人类社会而言,所谓的权威都有其相对的权限,这一原则恐怕才是真正最具权威的。不管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以及社会领域,抑或思想领域,盲目追求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权威,只能是愚蠢的徒劳。
但令人失望的是,此类“愚蠢的徒劳”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各级政府、各类行政部门无不打着“宏观调控或加强监管”的旗帜,行追求各自的权威之实。当然,正如上述,如果各类行政措施能够经实践证明是对全体国民福利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是在有着明确边界约束的权限意识指导下制定与实施的,那么,其“宏观调控或监管权威”也最终会得到国民的认可与敬重。问题是,看看最近,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还是各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一些措施,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自负”,行政触角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具体。似乎不如此,市场与私人主体就不能运行,就不会自理。而这些公共行政机构,在“保护市场秩序”、“维护投资者利益”或者“推动经济健康增长”的名义下,试图获取“严父慈母”的形象与权威,但在这背后彰显的却是这些机构及其代表“权限意识”的缺乏,太多时候忘掉了公共机构一切行为必须得到国民授权的原则,忘掉了其政策措施并非撒遍天下都灵验,忘掉了其政策必须是针对限定领域在限定程序上确定,也必须在严格监督下执行!
但愿国民授权下的所有公共机构都能认识到权威与权限的上述历史变迁及其实质,少些“愚蠢徒劳”的“权威追求”,多些“权限”意识与切实拾遗补缺的恰当行为。如果对这种良好愿望漠然视之,公共行政与国有企业及其主要掌控人员还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位堂吉诃德一样,老是沉浸在曾经有过的传统官僚体制、例行公事、程序繁冗的“夜郎自大”的“权威幻想”中,那么,随着市场和市民社会力量的快速扩大与增强,市场与公众迟早将会无情打破这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