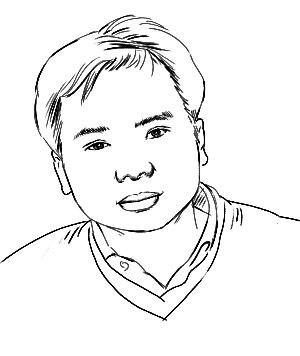|
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用牺牲企业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成长)做代价,用戳破资产泡沫、消灭社会财富的超紧缩政策,强行压制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信贷、投资、经济增速都掉下去了,但通胀依然很高,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样的调控成本,将是太高昂了。
⊙刘煜辉
尽管目前构成中国通胀压力的原因很复杂,但主导性因素是什么一定要把握住。这是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如果发生政策偏差,不仅防治不了通胀,反而会恶化通胀预期,使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
与上世纪90年代初因产品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不同,构成本轮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出现突出的产品供不应求情况。这说明通胀压力问题并不出在产品供需上,而在生产成本的推动上。
具体来看,有三方面表现。
其一,历史欠账要还。过去几年的低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严重透支结果。透支了要素价格(煤、电、油、运、水、气等资源要素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红利(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胀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透支了环境红利。既然是透支,迟早是要还的,否则只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经济失衡。
其二,透支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结构失衡,即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引致的国际收支失衡, 产生了反向“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因长期失衡累积的流动性过剩,首先推动的是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的迅速上升,同时工业部门也开始产生加薪的预期。
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国内农业部门产出越来越受到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所决定,加之美元泛滥所引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直接推升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因此,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
价格传递的最后阶段必然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和地价的上升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红利的消退。当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赶不上上述成本上涨的速度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倒逼着贸易部门制成品价格开始上涨来转移矛盾。我想,这就可能进入一个所谓的全面通货膨胀时期。这便是当下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的逻辑主线。
其三,中国现在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中国每年要消耗全球53%的铁矿石,全球每年新增原油需求的6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现在的原油自给率不到50%,一半以上依靠进口。美元长期疲软,加之次贷危机将全球资金都赶进了商品市场中寻求避险,导致原油、农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成本急剧上升的主要推手。
以上这些因素,显然并非都取决于中国,如果美国不能担负起全球经济调整的责任,延续垃圾美元政策以转移次贷危机的风险。中国将面临长期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但就中国自身而言,想要有效控制通胀,关键取决于企业消化成本上升的能力,核心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换句话说,在未来,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赛跑”将长期存在。
不过,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虽然严峻,但远没有国际投行最近预测的那么悲观。
大家都谈到最近公布的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至16.5%,觉得很忧心。但仔细分析,如果剔除受价格管制的两个行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以及电力,它们的利润分别下降了232%和61%)后,其它工业企业利润,大致增速为37.5%,较去年前11 个月还提高了近4 个百分点。
这一分析表明,尽管受雪灾、价格管制等扰动,实际上1、2月份工业生产状况还是良好的。这说明劳动生产效率加速进步的影响还在持续,说明企业微观面景气还在。
特别是机械设备、机电仪器等相对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仍然在加速(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35.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42.6%,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7.7%),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相当强。
如果美国次贷危机缓解,将会有更多寻求避险的资金从价格高悬的商品市场撤离,重新吸纳在信贷危机中被抛弃的资产,如美元、股票等。这样过去为了对抗通胀而买进黄金、卖空美元的策略就会开始变化。
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回落,对于那些吸收要素成本上涨能力较弱的行业来说,未来利润改善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在这一点上,国际投行的预测往往是短视的。
很明显,中国经济基本面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是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却是存在的。现在,特别要避免由于对宏观经济形势误判而导致的政策偏差所诱发的经济“滞胀”风险。
如果真正认清了中国这一轮通胀压力的主导因素源自于成本推动,那么当下的中国是否真需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压力中,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便成了一个“伪命题”。
事实上,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用牺牲企业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成长)做代价,用戳破资产泡沫消灭社会财富的超紧缩政策,强行压制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信贷、投资、经济增速都掉下去了,但通胀依然很高,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样的调控成本,将是太高昂了。
而尽管任何通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涉及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超紧缩政策(包括加息与升值,升值的本质就是通缩)致使全社会的流动性减少,但要素成本却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高升,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其本质是劳动生产率下滑。这是最要不得的。
只有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战胜了外部成本价格上升时,控制通胀才有可能。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只要同等数量或者略微增多的货币,反映的是人民币价值含量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值重估。这是经济增长的正常表现。
反转过来,当紧缩政策损伤到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那么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到有可能演化成恶性通货膨胀,最后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而告终止,进而陷入“滞胀”的泥潭,即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这是最坏的政策后果。
所以说,如果需求管理失效的话,就应该考虑调整调控方向。既然通胀压力短时间内下不去,就应该坦然面对,从供给上多下功夫,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解除制约居民消费的各种瓶颈,这才是当务之急。
这其实也意味着中国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而居高不下的政府储蓄率正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痛苦;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这样的话,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逐步改善,中国经济平稳走出通胀压力的泥沼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