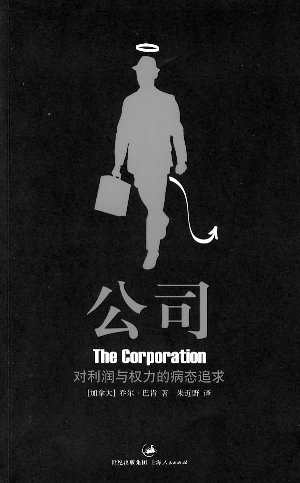|
商人,无论作为一个群体,或是作为一个职业,从来都是毁誉参半。《财富》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就理直气壮地宣称,“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F.A.哈耶克也为商人的逐利本能辩护,并声称,“把公共责任托付给商人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哲学家安·兰德则更进一步,甚至将商人对于利润的追求视为一种“美德”。同样,对于商人的批判,或者蔑视,无论中外,从古至今,都不缺少强劲的声音。
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同样也体现在商人所栖身的“公司”的伦理中,或者说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上。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公司使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发了商业思想者们出色的辩论。这样的辩论固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常见的议题,也在今天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商业界持续热烈的辩题。有人对公司兑现社会责任给予了极大的赞美,也有人认为,所谓的社会公共责任,对于“公司”们来说,实在是被夸大的使命。
一名研究法律的加拿大学者乔尔·巴肯如今也参与到有关公司问题的思考中,巴肯在其名为《公司》的著作中,对股份公司作为一种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以极其肯定的口吻表示,公司对于利润和权力的追求,已经呈现出一种病态。
在这位法学教授看来,公司如今统治着世人的生活,支配着这个世界;公司具有人的权利,却丝毫没有道德感,惟利是图;公司强调持股人的利益,不带感情,不考虑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股份公司作为一种病态的制度,拥有强大的力量,对公众和社会构成了威胁。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司所产生的影响与威胁也就扩散到了更广大的区域。巴肯据此认为,对于公司的破坏性行为必须要有限制。
如何看待巴肯的批评,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股份公司的力量,的确是当今这个世界不可忽略的。公司制度究竟是否真的那么充满罪过?如果像巴肯所言,因为制度本身的“病态”,公司的存在已给社会造成了诸多负外部性,那么,世人又该如何去限制和避免?
公允地说,巴肯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批评,确实有着一定的道理。比如,公司单单或过于重视持股人的利益,便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比如,公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或重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比如,也的确是在很多时候,公司因服从于自身利润追求而产生了相当大的负外部性,却想法设法逃避责任,而不是正视,等等。显而易见的是,巴肯式的批评很容易引发对公司制度不满者内心的共鸣。淋漓尽致的、不带妥协的批评方式,对于吸引掌声,往往很有帮助。
不过,也应当说,巴肯指出的是问题的一面,而不是全部。其实,乔尔?巴肯在他的著作中也叙述了公司制度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正是商业资本主义从萌芽时代走向发达的必然过程。公司制度的诞生,不是凭空落地,而是服从了资本经济的规律。仅从这点来说,巴肯把对公司制度的批评与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感结合起来,既不公平,也不妥当。
巴肯对于公司制度的质问,其实不难回答。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本身,就当一分为二去看。在相信古典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们看来,正是公司这种对于利润狂热追求的原动力,推动了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如果对这一点刻意抹煞,的确是不公平的。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公司的负外部性是可以,至少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公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同时,公司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主体。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能因为公司的负面作用而完全否定这样一种制度形式。举个例子来说,证券交易所也可能沦落为赌场,甚至比赌场还不尊重游戏规则,但这不能作为全盘否定证券交易所的理由。
在巴肯笔下,公司由于“惟利是图”,故不会对公共利益负责。而比起公司来,政府似乎是一个更适合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主体。这同样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如果简单认为政府比公司更能对公共利益负责,就得出必须加强管制的观点,那么很有可能会使得“公司”大伤元气。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不能一味强调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因为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公司的持股人,也包括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肯提出政府要向公司夺权的观点,显然是过于激进了。
在这本著作中,巴肯提出了一些对付公司制度的办法。这些办法听起来并不令人感到陌生。诸如增强调控机制、加强政治民主、创建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以及挑战国际新自由主义等,本质上仍然是针对公司制度的改良手段。尽管巴肯对于公司的批判毫不客气,但这位法学家并没有想到要“革公司制度的命”——这样一种态度与其说是巴肯不愿为,还不如说他无可为。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框架下,如果没有了股份公司这样的制度设计,还可以拿什么来替代?
在笔者看来,其实,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公司制度本身,而是一个社会能否有效地矫正“公司”产生的负外部性。很多时候,因为矫正的不力,糟糕的结果所产生的一本账,全算在公司制度的身上,这并不合适。而更要担心的,是强大的公司力量与行政权力过于暧昧的结合,却缺少约束,那确实是真正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