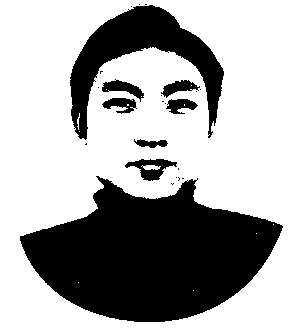|
在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被普遍看成是冲抵经济下行动能的重要支柱;各界认为税制体制和结构的调整有望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率;财政转移支付也被看成是改善环境、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石。财政部门要不负众望,承担起这些责任,成为国民经济效率增加的动力源泉,其自身得保持高效运转才行。然而,实际情况是,“高成本、低效益”一直是我国税收征管的潜在问题。审计署近日对税务部门征税成本开展了审计调查,揭示出人员支出水平较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无编制和超编制购置小汽车;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控制不够严格等四大问题。
关键是,这些低效率现象并不是不可摆脱的。依据《中国税务报》的数据,我国征税成本率(征税费用总额占总税收的比重)目前为5%至6%,而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以及英国的征税成本率分别为0.58%、0.95%、1.07%、1.13%和1.76%。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征税成本率一直处于上升通道,这也与发达国家征税成本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不同。1993年我国征税成本率为3.12%,1996年为4.73%,1999年已超过5%,此后征税成本率皆有增无减。这意味着,我国征税成本增速快于税收收入增速,越来越多的税收被消耗在财税部门本身。
征税基础设施不完善、纳税意识不高等因素自然是导致我国征税成本高企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但这些不是关键性的。我们已经看到,1993年来我国征税成本上升很快,很难说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征税基础设施水平在不断下降,或者说经济主体的纳税意识在不断下滑。并且,审计署公布的四点高成本原因其实无一与纳税基础设施或纳税意识相关,反倒是纳税条件看上去改善得有些过头了。
在笔者看来,财税低效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财税体制之内。这种理解蕴涵着更多的建设性,避免过分夸大各种客观因素,将财税低效率问题宽泛化,好像只有等到所有企业的征税平台完全建立,并可准确稽查,或者所有纳税人都主动足额纳税的时候,财税成本才能真正降低一样。
因而,降低财税成本,提升财税效率更务实、更有效的途径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我国财政效率近年来不进反退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体制设置本身存有诸多不合时宜之处。改革调整这些体制因素,正是提升财税效率的题中之意。
首先应转变征税目标框架。我国的税收之所以出现高收入与高成本并存的粗放型特征,乃是因为我国在较长时间内对税务机关只考核收入不考核成本。地方政府为调动税务部门完成收入的积极性,普遍实行税收任务完成情况与税务部门经济利益挂钩,且实行经费奖励的政策。这就必然促使税务机关在征管出发点上往往更多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组织税收收入,而很少考虑税收成本的高低。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产出最大化并不等于效率最大化。要降低单位税收的成本,就有必要引入正确的成本观念,强调成本意识。在业绩考核时,应该考虑加入征税成本纬度。
其次应简化财税体系。国税地税的分家也是造成目前我国征管成本偏高的重要原因。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方面,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机构分设后,人员大量增加,人均征税额增长不高,而人均征税额的增加低于税收总量的增长幅度,征收的效率实际上是下降了。分税制应该由分收分支更多地向统征分支转变,即在税收的征收环节考虑合并统一征收,减少重复人员编制,避免对同一纳税主体分别征税。1994年大力推广的增值税改革是另一需要着力改革之处。有证据显示,“世界之最”的中国征收成本,主要源于复杂的增值税管理成本支出。在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体制下,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防伪、运存、保管、使用、注销、审核、检查和监控成为一项十分复杂、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型势在必行。
最后应严控征税成本的扩张。为达到保障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的目标,我国征税机关逐步拥有了过多的自由权,尤其是在分税制体制下,地方征税机关实际上有把征税行为商业化的倾向。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只要征税“产出”大于人员成本,就会增加税收人员,甚至是编外人员。然而,税收成本绝不仅仅是征税成本概念,更主要的征税成本是税收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税务机关只考虑征税成本,则会造成显著的外部性。因为,政府从整个社会的税收成本的角度,严格规范征税机构及其行为是控制征税成本的重要一环。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提出了税收制度的四项原则,即公平、明确、便利、节约,这些标准至今仍焕发现实光芒。美国财政部宣布接管“两房”昭示,与转型经济相比,财政部门在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增加了而不是缩减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意味着,我国财政系统效率的提升将具有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