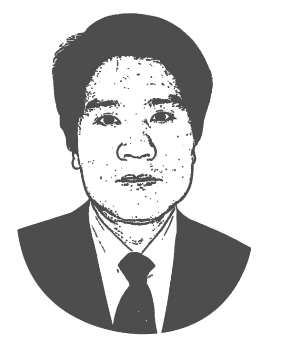|
正如央行发言人表示的那样,中国的金融系统运行良好,不会出现类似美欧的金融危机。例如不会出现次贷危机,尽管个别地区出现了贷款者断供的个案,但是,住房抵押贷款总体坏账率极低,是中国商业银行最优质的资产之一;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还不需要或者不足以支撑美国那样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的商业银行始终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投资银行业务和对冲基金几乎没有萌芽。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储蓄率,过度消费的习惯还没有形成。
但是,金融系统不出现问题,不代表实体经济可以永保安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缓慢回落,尽管CPI和PPI的上涨还比较明显,但是,如果除去油价上涨、粮价上涨、自然灾害等扰动因素,单单由于正常需求拉动所造成的通胀压力,是非常轻微的。CPI的逐月回落表明,通胀压力的释放已接近尾声。如果不恰当应对,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速下滑,将逐渐显现。甚至今后出现经济紧缩并非杞人忧天。
股市连续下跌,是一个重要信号。下跌肯定是众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前景的担忧是最为根本的。今年以来,出口增速出现多年未见的急剧下滑,引发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广东、浙江等地为数不少的企业破产,其中不乏大型的民营企业。作为企业优秀代表的上市公司,今年盈利前景也远不及去年,而只要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前景的预期恶化,股价的下跌就属于必然。也因此,这次央行降低“两率”和财政部免征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的效果,对于股市仅仅是昙花一现,欧美股市周一的大涨,也没对A股市场起到刺激作用。这又说明,沪深股市与外围股市仅有名义上的关联,我们的问题是对自身实体经济缺乏信心。
我们需要在增加政府投资和增加企业投资之间做出权衡,需要在依靠外需和依靠内需之间找到平衡,而将增长的引擎转为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才是经济健康发展、避免继续下滑的正道。
在一定的经济总量和国民总收入之下,增加居民消费,就要减少政府开支的规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种不正常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税收制度设计的缺陷,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且税负均过高。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行政管理费等支出超常增长,而社会保障支出却严重不足。居民收入一方面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本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消费不得不谨慎。
“建设财政”,曾被看做是中国财政的优越之处,在公共财政目标明确多年后,财政的建设色彩依然浓厚,淹没了财政的公共性质。但是,不但政府投资总体效率低于企业投资,而且政府投资支出又会挤出民间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
增加居民消费,除了增加可支配收入外,还要增强居民的乐观预期。在当前,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中国几亿城市居民是消费的中坚力量,他们把大部分收入投到股市,期望增值,以增加未来的消费,但股市的大幅下跌无情地销蚀了多年收入。在这个意义上,对股市需要拿出美欧应对金融海啸的勇气和决心,因为,保护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是保中国经济增长。
增加企业投资,减税是最典型的手段。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多次大幅度减税和退税。虽然降息和减税都有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但是中国降息的效果显然不如减税,因为能够获得贷款的企业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获得贷款凭借的不是盈利能力,而是特殊身份。也因为如此,它们对利率的微小变动很不敏感。民营企业对利率的变动本来要敏感得多,但是,过高的门槛,让民营企业贷款无门,利率的变动与它们没有关系。减税则不同,它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平行的,在经济大势不好的时候,减税增加了企业的税后利润,使企业的利润不至于下降得太厉害,有利于企业保存实力。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下降时,大家理当共同承担困难。如果一边是企业困难加剧,另一边税收却继续增长,就会进一步打击企业的信心。
美国的救市举措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一是行动迅速,二是力度大。也许有人认为这个规模仍然不够,但是对于捉襟见肘的美国财政来说,似乎已经尽力。
金融危机来得猛烈,但是治理起来从技术上却相对简单,但是一旦实体经济出了毛病,治理起来就困难多了。中国上次的通货紧缩从1997年开始,直到2003年才走出阴影。所以,未雨绸缪是必要的,既然解决“大小非”痼疾、增值税的转型、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现在就是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