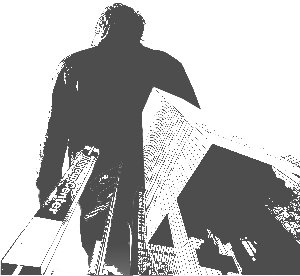|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经过艰难的决策,期待了三年之久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出台,各种猜测和争议自然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政府重新成了医改方案的主角,无论是时机的选择,还是实际的政策效果,都可以说恰逢其时。应该说,新医改方案有了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作为这个医疗体制的直接相关者,我们都将从此次医疗改革中得到更好、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是一个国家实施体制改革的基础所在。但是,医疗改革,不论是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世纪性的超级大难题,力图通过几次改革就能实现尽善尽美基本不太可能。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票友理论家》(The Accidental Theorist)一书中就说,美国医疗体制虽屡经数次改革,但医疗费用非但没降,反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反弹。在这场被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家约瑟夫·纽豪斯戏称为“医疗浪费的鸡尾酒会”的医疗改革中,传统的医疗保险方式并没有给医生提供思考医疗成本的动机。长期来看,医疗成本仍会呈现出“水平线”,也就是医生会不计成本去探索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例如,美国在1983年医疗体制改革之后,就已不再支付医院的所有成本,而采用定向定额的方法支付。政策实施之后,平均住院的天数大幅度减少,同时对医疗质量也没有产生明显副作用。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住院的成本又开始上升了。
这就是说,医疗行业具有特殊的规律,医疗改革就如患者服药一样,在长时间的服用某些药物之后,会产生药物的物理适应性,此时再加大剂量也无济于事。我们必须要寻求新的药物,或者新的改革方案。这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内在发展性,必须要在颠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是长久之计。
所以,此次医疗改革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用好8500亿投资,尽管投资对于一项改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投资之外的社会技术则更加重要。套用那句现在非常流行的话,改革的关键还在细节处。如果对新医改还有些批评或者改进意见的话,那就是在实施过程中如何把握住每一个细节。
根据意见第七条,“建立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体系,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千万不要能忘记,这中间还有个常见的“通病隐患”。理论上说,能够实现国家招标的定点生产或者集中采购固然好,但要真正做到,做好这点,可能要花费更高的监督和实施成本,以确保这些环节不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或者滥用。一旦某个环节出了差错,那么整个生产和流动环节的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
在原有的体制中,虽然由于医药勾结的腐败导致了医疗费用急剧增加,但仍会有些民营医院通过提供降低医疗费用的途径来吸引大批低收入或者无医保的患者。所以,在原有的医疗体制中尽管存在一定的腐败可能性,不过这些腐败仍是非系统性的。一旦实施国家采购,直接配送的一体化手段之后,如果不存在腐败,那药价可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原来的体制应该是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行为。但这还有个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透明的、不可操纵的。如果被某些人所操纵,那意味着所有的医院都必须接受他们的管制性要求,就会产生一些系统性的腐败行为。这可能就变成比原来更加糟糕的制度安排。原来的制度虽然不好,但是毕竟还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压力和一些企业家的创新动力。现在完全交给了政府来做,那意味着所有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创新动机都被压制。这对国有的公立医院来说并不受多大影响,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医生队伍和技术实力为后盾,而市场上的医疗消费是具有刚性的,这使得大量的消费者在同等医疗费用的条件下会从原来的民营中小医院转向公立大医院就诊,那么私立的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冲击。
所以说,要使一个具有良好意愿的改革处于真正的良性动态发展过程中,关键就在把握住每一个细枝末节的小环节。克鲁格曼这只美国黑嘴的刁钻的确是有些刻薄,但他在《票友理论家》一书最后所说的那段话实在很中肯:“使医疗成本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贪婪,也不是低效率,更不是老龄化,而是科技的进步。过去的医疗成本不高,不是由于医生廉价,或医院管理有方,而是因为不论如何人们愿意支付多高的代价”。
只要在技术许可的条件下,人们对医疗需求的弹性是无止境的,这样的人类认知条件必然决定了我们今天对医疗的改革需求是内在动态的。
细节决定改革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