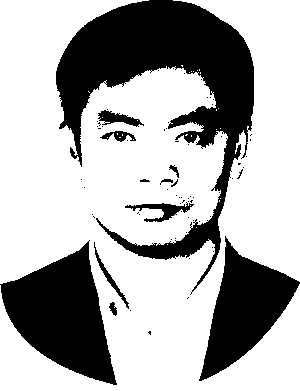|
正如IMF总裁卡恩在对朱民的评价中所说的,对朱民的任命,非常重要的考量是以此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依此逻辑,自成立以来主要代表“富人俱乐部”利益的IMF,有可能因中国话语权的扩大而加快改革步伐。而中国央行在关于朱民任职的回应中,亦再次表达了呼吁IMF进一步改善其治理结构的愿望。
先得承认,假如没有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IMF中的配角地位几乎不大可能有大的改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现在,即便是美国,也格外担心自己能否继续维持金融主导国地位。当然,美国人毕竟老辣,刻意在不久前通过罗伯特·佐利克放出风声,颇为煽情地呼吁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比例进一步增至50%,认为世行的改革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
其实,两年前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既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肯定,更是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林毅夫在佐利克领导下的一种责任担当。况且美国人早就看出,世界银行在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有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人接掌了世界银行行长之职,大概也不会对美国根本利益产生多大影响。但IMF就不一样了,这个战后世界经济权力符号表征的“最后贷款人”,是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的“领地”。 在备受诟病的IMF治理机制改革问题上,更大程度上代表美国利益的卡恩就曾声称: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需要新体系,但IMF职责改革仍无路线图。事实上,不久前,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公报就拒绝了中国要求IMF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的建议。决定“采用现有的份额公式作为工作的基础”,来实现将至少5%的IMF份额“从代表性过度的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并轻描淡写地就其自身改革做出了“打算在下次会议上采取一个公开的、建立在资质基础上的、透明的IMF管理层遴选机制”的说明,凸显作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堡垒,IMF在维护既得利益国权益方面是多么不遗余力!
只不过,今天的国际政经情势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1944年相比已大大不同了。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机制改革正在到来,这是不以发达国家意志为转移的。在此情况下,IMF更应审视的是如何适应业已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洗牌,通过自身建设性的改革来确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新坐标,而非一味拖延改革或者转移改革视线。因为假如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世界银行迈出了自身改革的关键一步,则作为战后世界经济权力符号表征的IMF将越愈显得孤立。
但是当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策略,更要有能够引导国际金融话语权并有相应国际声望的专业人士为支撑。换句话说,假如西方国家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愿意赋予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更大的行为空间,则届时中国必须能派出更多类似林毅夫和朱民这样的国际型人才。而就国内的存量金融官员以及金融专家结构来看,金融专才尤其是战略人才的欠缺,恐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中国布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瓶颈。
应当说,这些年来,通过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战略性金融人才正陆续成熟起来,并在主要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担任要职,也出现过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章晟曼等出色代表。不过,整体看来,中国在介入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方面的现实能力不仅大大落后于美欧和日本,甚至比不上印度、巴西乃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仍需加大努力,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和造就一批能领军金融强国建设和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专业人士,争取使他们尽快进入到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任职。我们在期待这些专业人士在与国际同行 “跨情景的对话”的同时,更能在关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规则、概念、议题甚至整体制度框架上拿出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建议,进而提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机制设计范式,全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