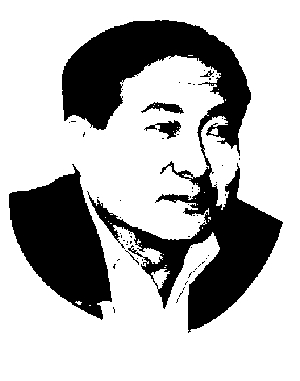|
孙 涤
我在本栏上期试图向大家说明,“明天”的股市不可预测,还是谦谨一点为好,别老想着击败市场、“抄底”或“逃顶”那类的好事。若你真想要挑入市时机的话,恐怕是翻皇历也比听股评忽悠来得强,基于人们的信念——投资是一种信念游戏——除了自己之外,你至少再没别的对象可去抱怨了。
不过有一点还须注意,就是不管明天的股市好坏怎样,你都得和其他投资人互动:整个市场的饼即使缩小,你仍旧可以分到更大的一块;反之,市场的饼扩大了,也不能保证不会赔得光光的。证券投资之所以能风靡全球而经久不衰,就在于它的人际博弈性质,于是人们都有兴趣探询,“哪些在明天会更好?”
先来看看两个卓有成效且为国人所熟知的理财家的判断: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格罗斯(Bill Gross)和GMO的格兰桑(Jeremy Grantham)。我喜欢他们的洞见和直言不讳,曾借他们的意见来壮过自己的胆,还打算以后常常引用他们。
格罗斯对今后十年全球经济的趋势总体上是看淡的。他认为过去几年的折腾,弄得整个世界锐气大挫,修补起来非常费劲。政府和民间都会降格以求,接受一种“新标准”(New Normal),满足于较低的成长率和回报收益。如果说在2000年至2009年间大家对经济增长的期望是3%至4%的话,那么今后十年的预期就会满足于1.5%至2%。对投资收益的期望因而也会减半,从以往的10%至12%降低为5%至6%。扣除预计2%至3%的通货膨胀率,实际的回报仅仅2%至3%而已。格罗斯对发达国家的前景也不看好,他认为在这些地区,组合投资的收益是为了保值,用来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要谋求发展,就一定得走出美国,进击一些新兴市场,比如巴西、中国及其他亚洲的资本市场。他的理由是,这些新兴市场不但投资意愿强烈,财资也已经相当雄厚,这是发达地区在数十年前力求推动全球化的时候所始料未及的。
相比之下,格兰桑对美国的状况要乐观得多。他不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有什么结构性的下降,而是相信美国股市仍能维持历史的平均水平(扣除通货膨胀后6%-7%的年增长率)。他不同意格罗斯的“新的低标准”,反而认为美国的一些绩优大公司(约占30%)的前景甚好,能更上一层楼。在投资国际化的观点方面,格兰桑和格罗斯也大有出入。比如,格兰桑认为,新兴经济体,控制大于管理,社会—政治的不确定变数很多,随时有可能出毛病。他的见解是,在当今资本的全球配置新格局下,国际化虽然势不可免,但方向上还得周延考量。由于新兴市场发展前景迅猛,那里的公司股票的市盈率过高,并购对象的定价也趋向昂贵,这都在聚积风险。同时,格兰桑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等)迅速致富对资源的需求影响,他认为包括各类金属、能源等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扬趋势是难以遏制的。
看看两位大师在他们本行的判断上竟是如此大相径庭,教你不得不意识到,经济乃是人类的博弈,而不是什么严谨的科学。要是在两位物理学大师之间,如此冲突的见解,只可能发生在哪个女孩子更漂亮些,哪首歌更好听点之类的判断上,而不会发生在本专业上。不过我想,格罗斯和格兰桑都得像任何具有求真务实精神的人一样,认同一些基本的事实。今后的十年,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将面对过去十年闯下的5D困扰(Debt、Deficit、Dollar、De-leverage、De-globalization,) 即怎样解决欠债深重、财政赤字、美元疲软、降低杠杆率以及“去环球化”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日本人修复企业的财务亏损状况,努力降低杠杆率几近二十年但成效不大的历史来看,格罗斯的顾虑确有其根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大衰退》,辜朝明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至于美元的贬值,从美国民众沉湎于透支消费、福利薪酬高居不下、拒绝承担税负,而政府只能靠举债支出,以及受利益集团操控的情况来分析,不难明白这是迟早会发生的。
同物流的环球化趋势有可能式微恰好相反,投资的资金流的环球化将有增无减。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股市的波动和世界市场的波动可谓亦步亦趋,风险的正相关性高达90%,十年前才50%而已。因此全球范围内逐利而动、配置资本的动因非常强劲。事实上,依据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编制的MSCI全球指数,全球的投资结构已变成了:42%在美国,45%在其他发达地区,新兴市场占了13%。对美国人来讲,他们还是最大的“金主”,虽然越来越起劲地忽悠日本人和中国人来为他们的国债买单,他们钱财高达72%还是投在了本国的股市,这种状况在今后十年可望有很大改变。无论格罗斯和格兰桑都认同这个趋向。
那么,国际的巨额资本要投向哪里?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国的理财界有人分析,过去十年间投资新兴市场中的拉美国家 (如巴西)的回报,要高出东亚至少两倍。亚洲市场的市盈率普遍明显高于拉美市场,买的时候就不便宜,亚洲新兴国家的高成长因此未必能够带来高收益。这种貌似合理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下期来谈。
如果说这一次金融海啸带来的市场崩塌能给世界什么教益的话,那应该就是必须De-learning(“非学”,借用韩非子的用语):人们得摆脱牵强不实的经济理论和对人的行为的虚妄假设,这类观念假设有不少是在意识形态的局促里被硬挤出来的。摆脱谬误观念的纠缠和束缚非常之关键,缺少了这个“非学”的D,前述的5D困境仍将不断重演。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