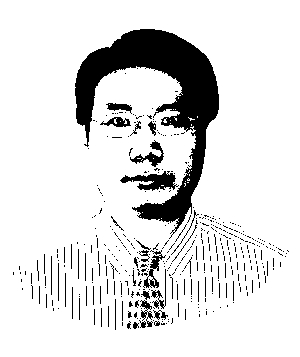|
目标者,只能存在于未来预期之中。一旦实现,就不再成其为目标,只能是确定和实现新目标的基础。目标和预期不可分割。改变预期,就意味着调整目标;调整目标,也意味着预期发生了变化。预期是意识和信念的反映,意识和信念则取决于历史经验的累积。从这个意义说,预期就是基于过去而对未来的推断和预测。一方面,这种推断和预测不可避免地有着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它们又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当前行为。依此认知,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很多事情。
1995年4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第一届阿尔文·汉森公共政策论坛上,围绕着MIT教授索洛和斯坦福大学教授泰勒提交的有关货币政策是相机抉择还是按照既定规则决策的主题论文,学者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
在索洛等人看来,央行只能根据实际经济形势,尝试性地谨慎地,但又不失灵活地确定和调整货币政策。而泰勒等人认为,基于时间不一致性、预期、可信度等因素,央行应确定一系列规则,针对某些关键经济变量设定相应的目标水平,以此为央行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行为程序。能够设定量化目标水平的指标包括通胀率、失业率、货币供应量,甚至利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比如,一旦超过2%的容忍水平,央行就可以实施紧缩政策。这被经济学界称为“泰勒规则”。
其实,今天看来,这种争论没有多大意义。在最早也最有力倡导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作为宏观调控的两种政策均是相机抉择的,无非是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政策,衰退时实施扩张政策,只不过,对过热和衰退的判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判定的依据也不同。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就试图为货币政策制定“规则”。最典型的是,他主张为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设定一个目标幅度,比如4%,超过时则施以紧缩政策。如此,就可以由一台计算机代替中央银行众多官员,自动对货币水龙头施加调控。
所谓新派的“泰勒规则”,犹如弗里德曼的巨型计算机,都属于“规则制”:试图以预设的参数目标,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依据,依此减少人为随意因素,进而防止货币政策的偏差。可是,现实中,不仅难以确定一个作为客观标准的参数变量及其目标水平,而且依此行事,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偏差。无论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量目标,还是泰勒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抑或是实际GDP与潜在GDP的缺口,以及失业率目标,所有这些可能被盯住的经济参数计算及其目标水平的确定,无不以某些特定的假设为前提。问题是,这些假设合理吗?况且,将盯住参数的目标水平定为多大才符合客观形势,也难免有着很大随意性。所以,完全按照“规则制”来确定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央行的低效甚至失职,结果与预期恰好相反。
最近的教训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按照“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调整标准没几年后,便发生“次贷危机”并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尽管作为传统上衡量通胀水平的指标,美国CPI在危机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以此为目标规则的货币政策也就处于相对宽松状态,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证明,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对危机的形成难辞其咎。如果不是大量流动性的泛滥,怎么会有房地产泡沫及其破灭所带来的危机呢?只不过,膨胀的货币被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的资产市场所吸纳而已。
因此,仅仅将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目标作为美联储行为的依据,极大地忽略了金融资产市场对过多流动性的吸附,以及这种资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忽略了金融衍生市场对货币流动性的创造能量:当今的货币创造,不仅来自传统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业务,也日益来自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市场,比如,抵押贷款的多次证券化,无疑扩张了货币流动性的派生创造能力。其结果是,CPI,即美联储盯住的通胀率,倒是在既定目标范围内,但超级资产泡沫及其带起的经济过热如火如荼地升起,只是不在央行的视野之内,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抑制举措,反而在政策措施和信号上一再放纵,直到泡沫破灭并带来了比恶性通胀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见,央行如若遵循所谓的“完全规则制”,不是刻舟求剑,就是削足适履。
实际上,在纸币本位时代,货币界于国家和市场之间,不可能只依赖一头。作为现代纸币管理机构的中央银行,其所作所为,只能是一种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寻求均衡的政府行为,肯定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确定和调整货币政策的基本行为,也只能是央行根据对市场和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谨慎而尝试性地相机抉择。当然,政府行为的属性,又决定着央行是在既定政治框架约束下行动,因而,随着经验的积累,也就会形成一些行为规范,但这并不能否定货币政策是央行相机抉择的结果。
随着经济系统,特别是金融资产市场的扩张和深化,经济受到外来“突发事件”的冲击越来越频繁,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央行,视野应不断放宽,在更加谨慎的同时,理应根据新变化及时灵活地确定和调整货币政策。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