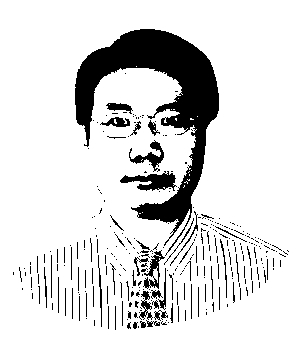|
袁 东
究竟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主要决定着汇率形成与波动?这个问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时就已存在。只是现在,答案已变得很显然:资本项目和资本交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汇率主要由资本项目决定。
1971年之后,以固定汇率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走入了历史,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无体系”时代。没有了贵金属的基准支撑和制约,汇率基本就浮动了。在教科书及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谈判桌上,经常项目被视作决定汇率的主导因素。以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或逆差,也就是商品与服务贸易情况来评价汇率水平,进而提出政策调整要求。但只要粗略比较当今全球贸易额、经常项目发生额与差额、货币与资本交易额,就可明了这种认知早已偏离了实情。
先看各类外汇工具的日均交易额,1998年超过1.5万亿美元,2010年接近4万亿美元,而2009年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额日均仅858亿美元。再看非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占比,从1998年的17%降至2010年的13%;各类金融机构的交易占比,从1998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87%。这些由金融机构主导的货币资本交易,主要发生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每天巨额交易中的65%是跨境交易。而且,这些交易主要是以衍生品方式进行,现货交易仅占2010年全部外汇交易的37.4% 。
这种状况,是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进入浮动制时代的必然结果。一旦汇率脱离了某种基准牵制,国际融资在由官方主导向私人金融机构主导转变的“私人化”过程中,种种所谓金融创新及由此带动的货币资本交易,就如脱缰的野马,狂奔而去。
远远超过贸易额和经常项目收支差额的货币资本交易,无疑成了外汇市场上的主导者。而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又是货币资本交易的主导者。所以,汇率的定价权并不在实体企业,也就不在商品与服务贸易领域,金融力量已然成了当今世界的汇率定价者。
现今的金融力量,基本把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由此,汇价的主导权也就在这些国家。如果说汇率有操纵,那也是金融机构在操纵,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在操纵。
当然,这并没有否定经常项目收支差额的影响。只不过,这一原本决定汇率的基础性因素,已被日益快速膨胀的金融交易,仅仅当作题材不断炒作,进而不断被扭曲,以至在汇率波动的轨迹中看不到多少影子了。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国内金融市场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国际金融交易与货币体系中,更没什么影响力,暴露在外的,基本是过去十多年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但他们还没有多大力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去对冲和平衡。因此,似乎贸易和经常项目就成了这些国家汇率低估的证据。
如果以汇率为借口,渲染全球经济的所谓“失衡”状态,那也首先是由金融市场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诸如索罗斯总结的“超级泡沫”所导致。而这种失衡,因金融市场交易及其主导权在发达国家,所以,责任也就在发达国家。再说,失衡与否,要看站在谁的角度讲。世界经济什么时候没有“失衡”过?在发达国家认为不失衡的年代,可曾问过发展中国家的感觉?所谓“均衡”,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不切实际的假设,而全球经济从来就是在非均衡中运行与增长的,如果完全均衡,意味着没有了落差力量,就像水流没有了落差而不流动一样,全球经济也就没有了内在增长动力。
由此观之,不符合现实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是多么荒谬。更加荒谬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占全球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历任决策者,都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了几乎唯一的决策理论和智慧来源,以至最后捏出了“华盛顿共识”,硬要推销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实践证明,诸如俄罗斯等无条件接受这种推销的国家,无不陷入了同当初预期相反的被动局面。
实际上,当全球货币制度完全进入纸币本位时代后,货币无一不是“国家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超主权货币”已不存在了。即便是已运行十多年的欧元,也是以这一货币联盟成员国放弃了一部分民族国家权力为代价的。在这种货币制度下,货币的发行流通及其价格,是由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共同决定的。以纯粹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显得不合时宜。由此,作为货币价格的汇率,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在所难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现了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现实。
总之,汇率有市场决定的一面,也有难以避免国家因素影响的一面,这意味着主要经济体间的政策协调,在全球治理建设健全中是必要的。值得提醒的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不可替代,两种力量也应有合理分工和搭配。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在认识和行动上,全球的精英们是否会表现得比第一个十年更好呢?这取决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