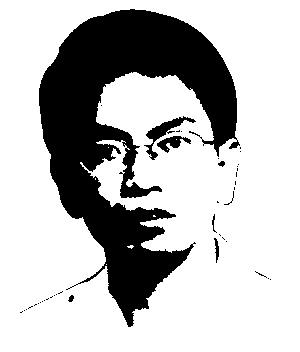|
倪金节
伴随着国内通胀势头攀升,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的迹象十分显著。
刚刚过去的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从6.63升至6.54。如果从去年6月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算起,人民币累计升幅已经接近5%,由于越来越大的外汇对冲压力,各方对于升值的严重抵触情绪渐渐消退,在存款准备金和加息等常规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空前之后,升值,渐渐成为市场主流预期。
眼下的情形与三年前十分相似。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开始进入“6.0时代”,季度升幅高达4.3%,而上一轮通胀8.7%的峰值即出现在当年2月。如今,央行再度升息预示着3月CPI极有可能再度超出预期,本轮通胀峰值或许未到。种种迹象都昭示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胀都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但升值能遏制通胀吗?从逻辑说起来其实很多人将信将疑,也有人说这话听起来像是美国人的阴谋。
的确,从过往经验来看,升值遏制通胀的逻辑不怎么说得通。比如,2006年到2008年,人民币“破八又破七”,但CPI涨幅则从2006年1.5%升至2007年的4.8%,2008年更升到5.9%,升值幅度累计高达20%。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上一轮通胀最高峰期。
近在眼前的事实,让升值治不了通胀的论点似乎成为真理。不过,各位别着急,故事还有另一面。
按照经典的理论,在一个市场化经济体,本币升值之后,进口价格必然降低。中国当前主要进口各种资源、能源产品、设备和零部件等生产要素,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可能对冲这些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部分。过去五年,之所以小步慢跑一直是主基调,不排除主要是基于政治考虑。因为小步慢跑有助于不断强化升值预期,从而热钱流入也就具备了长期性。
还有,海外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并不是人民币升值所能企及的。在欧、美、日纷纷量化宽松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动性呈现海水式泛滥局面。国际资金在商品市场的恣意炒作,所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涨跌速度和周期,远远不是货币升贬所能同步应对的。比如,伦敦市场的铜价可以在数个交易日从每吨8000美元涨至每吨9000美元,人民币汇率能设想在短短数天内达到如此升幅吗?
因此,希望通过升值降低进口产品价格,对冲国内企业成本的上升压力,可以想象难度有多么高。这也就是说,升值没能遏制住通胀,问题关键不在于基本原理错误,而是因为升值幅度远远不够。加上小幅慢跑,热钱肆意泛滥,让这一问题更为看起来无解。
当然,决策当局是不可能允许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的,因为这对于低附加值的出口外贸企业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大量制造企业工人会失业,这也是中国社会经济难以承受之重。不过,2005年7月汇改至今,人民币升值20%以上,意味着我们购买外国物品的成本降低了两成,而由成本降低带来的进口扩大,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胀势头,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可以肯定,如果目前人民币依然处于2005年之前的高位,由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可能更为离谱,国内的货币超发压力也会比现在更为严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感谢这些年来的人民币升值。
当然,历史经验说明,汇率博弈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当本币大幅升值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一次性大幅升值,往往预示着资产泡沫盛宴的结束。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对泡沫化的难题,社会氛围浮躁,加上国际炒家屯兵香港虎视眈眈,让人民币升值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色彩。以国际炒家的算盘,力压人民币大幅升值,无非是为了继续让中国资产泡沫膨胀,掩护国际热钱安全撤离。姑且不论海外此类报道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未雨绸缪总不会错。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打破“人民币必然单边升值”的预期都十分必要。因为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和外币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谁必须单边升贬的逻辑。
所以,笔者以为,人民币宜采取扩大波动幅度的方式,来应对热钱肆意泛滥的问题。当国际资本纷至沓来时,如果我们依然采取之前的小幅缓慢升值的方式,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如果采取一次稍大幅度的升值,同时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给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创造比较大的空间,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前几年走过的弯路。
经过30多年的经济起飞,中国的工业化正走入中场,货币价值理应重新评估。提高名义汇率或高通胀都是与之形影相随的经济现象。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物价形势,人民币升值或许不是最佳之策,但肯定是必不可少之计。任何政策的执行都有成本,升值会给出口企业带来巨大阵痛,但要是如果没有忍受阵痛的勇气,没有权衡轻重的智慧,我们有怎么能跨过这个坎呢? (作者为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