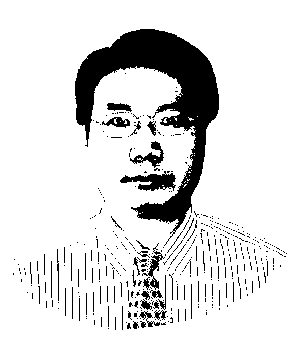|
袁 东
毕生研究经济变迁的道格拉斯·诺斯教授一再强调,如要真正透彻理解包括兴起和衰落在内的经济社会变迁,除了人口和知识因素外,将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凸显出来,作为重点予以分析,是其中的关键之关键。
在这位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看来,那些能够兴起并能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从而长盛不衰的社会,都会呈现出一种适应性效率特征:能在遇到重大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时灵活调整,整个社会有着很强的弹性。对此,诺斯教授是这样界定的:“我所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是指当问题演化时,社会不断修正和创造新制度所不断需要的条件。伴随适应性效率的一个要求是政体和经济体能够在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时为不断的试错创造条件,消除已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制度性调整。”
可见,诺斯的适应性效率,取决于一套能真正对尽可能广泛社会群体具有激励功能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在面对非各态历经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时,将会灵活地尝试各种选择,以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制度结构也需要一种信念结构,来鼓励和允许进行实验,同样也消除失灵。”
当一个社会的公权力结构是依循自上而下的原则形成时,政府官员体系更有可能趋于封闭、守旧、固化,也就更容易成为制度变革和适应性调整的阻碍,现实的政治结构也就更容易受到侵蚀,一时的秩序更具脆弱性,秩序和失序的转换会由最初的微妙变成后来痛苦的决绝与煎熬。所以,真正吞噬一种制度的是既得利益团体,尤其是那些掌握着公权力的各级官员。
就现有中国经济格局而言,是由30多年前财产资源几乎完全被行政化控制的高度集权化大一统起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抽离出非行政控制的市场化成分,演化形成了行政化和市场化共存的局面。且不说,这一过程中的非行政化基本上是从行政控制系统而来,仅就目前市场化部分看,也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着行政系统。因为,伴随审批、清退、强拆式没收、土地强圈、低补偿性没收等强制性行政手段的大量回归,在大型国有企业借助行政力量长驱直入以强化其控制性地位,并将大部分银行信贷资源低价占有的过程中,私人产权、行业经营的私人自由进入权、市场化定价力量等都受到了挤压。
在从一个财富几乎全由行政系统占有中慢慢分离出非行政性市场化部分时(当然不只是存量,尚有增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还有各类行业与资源经营许可,以及诸如教育获取资格等),全社会可以划分成三大利益集团:行政系统、市场化系统,以及那些既没有占有行政性利益也没有获取市场化好处的集团。
在这一社会分化过程中,行政集团手中握有的公权利,既有可能继续获取传统体制下的利益,又有可能获得市场化的好处。市场化集团也可进一步分化为依赖于行政集团获取市场化利益与从社会边缘或夹缝中生成的市场主体两类。行政和市场两大集团会在市场化力量催成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就会结成新的利益集团。
而除此之外的那个庞大团体,当然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可能取得绝对生活水平的提升,有些成员也可能在市场化过程中通过奋斗和机缘脱离本团体,但这是就动态过程看的。但即使从动态看,在一个社会集团的分化和固化步入了自我累积性滚动过程时,这种脱离也是少数的。所以,就某一时点的存量看,那个庞大团体中的绝大多数处于一种缺失话语权的弱势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尽快加以切实有效调整,这一过程起初可能缓慢地随后可能加速形成如下格局:为了行政利益与市场利益的均沾,行政权力控制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深度上扩张,或者向传统体制回归,以致即使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如要维持其地位或进一步扩展,也不得不在原来成本基础上加入不断增大的同行政集团交换的成本;更不用说那些一开始就依赖行政团体的市场主体,他们更会因成本的增大而促使自己进一步寻求行政权力的庇护;而那个原本就话语权的第三集团,则会在越来越被动的现实及心理失落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大的不公平感和不满心理,而这又加速了前两个集团的合流。若是如此循环下去,社会脆弱的秩序很容易转为无序。
为防止这样的循环,我们非常需要那种鼓励和允许试验的信念结构,哪怕试验仅仅是一种冲动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的冲动,而不需要那种非此即彼的先验式束缚框架,这是根本和首要的。在此前提下,我们首先需要试错,其次需要为试错创造条件的制度及其调整。我以为,这是中国兴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