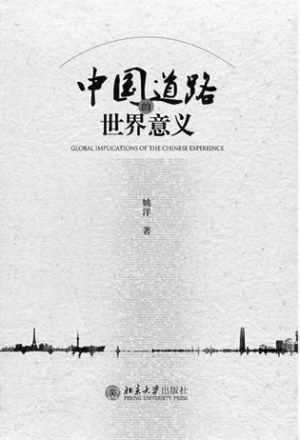|
⊙李牧之
差不多6年前,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一次论文报告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姚洋教授。那次报告会是专门为他举办的,主讲他的新论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偶然的一次相遇,颠覆了我对姚洋的认识,原来姚洋是如此陌生,完全不是在以往论文读到的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形象。那篇论文对姚洋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他非常明确地宣告了他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自那以后,包括这篇论文在内很多文章,招至经济学同行的严厉批评,并将姚洋归为新左派。姚洋亦直承新左派(他定义为左翼自由主义)的身份转向。这一转向,或许可以从姚洋教授的新著——《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窥视一二。
林毅夫、姚洋、张五常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30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这包括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以及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当然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林、姚等人的这一判断存在疑义)。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就有两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成功?中国未来应该怎么办?《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书的四大章,围绕的主线也正是这两个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姚洋明确表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这亦是灵活采纳“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结果。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
对过去的解释意在揭示未来的方向。在姚洋看来,仅用经济发展替代社会一切问题的老药方就要失灵了,以增长共识为核心的执政策略,存在大量副作用,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财政对公共服务的缺席等。中国如要继续发展经济并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多的民主和法治以外,别无他路。民主的实施不应因中国国情而有所区别,法治的建立必须先从国家权力机关开始。
核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亦即姚洋所指的右翼经济学家的这些主张,构成了当前社会思想图景的一半。对这些解释,姚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分歧不大,与他自己定位的“新左派”的其他学者所不同的是,姚洋受过主流的专业经济学训练,他清楚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根源是什么,并且观点一直未变。显然分歧并不在彼岸的选择。姚洋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合适的改革路径以达到这些政策”?也就是“如何选择彼岸”?
姚洋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不偏向任何社会集团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的政府。这是中国有别于他国的主要原因。据姚洋的总结,中国“中性政府”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基础: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贤能体制。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线的一系列革命产生了平等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过渡的准备工作。而政治上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淡化意识形态,选贤任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保持了相对于中国社会的中性态度,把发展经济作为其执政的重点工作(亦即增长共识)。
结论的缤纷多样,或许这是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环境的切身感受不同。以中国经济是否可称为奇迹为例,林毅夫等人研究转型经济时,还特意将俄罗斯、东欧等的转型衰退作为中国成功的对立面。但在中国奇迹之光闪耀全球之时, “东欧国家在经历了90年代初转型期的阵痛之后,在过去10年间纷纷走出低谷,成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东欧国家中转型最顺利的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2010年的中国人均GDP不到上述国家的四成,中国转型真的是奇迹吗?
制度的转型是困难的,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中表示,“经典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响,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俄罗斯转型时,索尔仁尼琴在痛批叶利钦自由主义的药方——休克疗法的荒谬的同时,不断地警惕人们不要因剧变后的转型艰难,而把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戏剧化地过滤成甜蜜的回忆”。
梳理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道路方向选择,往往是时代危机后的结果。“文革”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小岗村农民的勇敢实验的产物。
正是 “亲身体验”的不同,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多种解释和未来道路方向的分化。姚洋所论只是这条分水岭的一个镜像,代表了中国发展路线认识的一种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