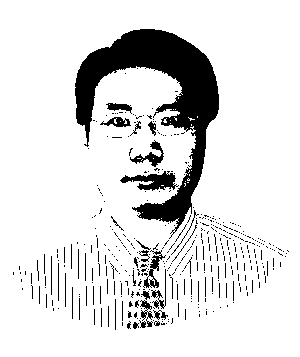|
袁 东
温州部分民企今年以来深陷高利贷漩涡,资金链条断裂,以至几十位企业主“跑路”。这些努力创业并有贡献的企业家走到这种地步,令人遗憾,也发人深省。
我由此想到了一个问题:加工制造业不受重视,产业地位下降,经济过分追逐金融化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放任那些私营企业主转让一手创办并经营多年的企业,将变现资金投入股票、房地产、债券、基金以及矿山、金融机构的股权,专事直接或间接性的资产投资活动的现象蔓延,那将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投机性金融和食利阶层膨胀的过程。这是否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呢?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答案都是否定的。
眼下,在那些过分追逐金融战略、将金融服务业作为重要支柱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美英两国,愤怒的失业和低收入人群已走上了街头,这种“过来者”的社会分裂教训,昭示着涌向金融投机活动的潮流若是肆意泛滥,前景堪忧。
稍稍拉长历史观察镜头,过去五百年,凡全球最发达的国家,每当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时,一般都是其最顶峰期,但也是制造业等产业空心化或者去工业化最严重,输出资本到海外投资最高峰,社会财富最为集中化,贫富差距最大的时期,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不用多久便让位于后来的新兴挑战者。美国能否跳出这一魔咒?就目前的情况看,很难!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几十年,从墨西哥和南美洲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成了世界首强。但源源不断的贵金属输入,推高了国内物价,并使银行借贷、债券买卖、金银及其艺术品收藏和交易过度活跃。人们开始鄙视生产性工业和商业活动,纷纷转向那些能轻松赚钱的投机性金融炒作,而原来作为经济支柱的毛纺织业和钢铁业逐步衰落。以1596年王室破产为标志,西班牙走向没落。
荷兰的造船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糖类精制业等在18世纪中叶盛极一时。但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因为过度关注金融,制造商和贸易商被排挤出高收入行列。到18世纪中期,经济史学家统计,城市管理者和公司董事收入的57%用于购买国债,25%用来购买股票和国外基金,12%用于购房置地。对债券、股票和国外基金的持有量成了财富和地位的衡量标准。这导致了工业和商贸业在18世纪50年代陷入困境,失业人口迅猛增长,贫富两极化日益加重,曾经的繁荣变得衰败不堪。
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十九世纪成了全球工商业中心。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英国人狂热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以及对外输出资本。大约三分之一的贵族是金融和铁路企业的管理者,但极少在制造业生产企业任职。1914年英国对外投资40亿英镑,占当时世界投资总额的43%。但在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同时,基础产业走向了衰落。1913年,占英国总人口1%的富人拥有了全国财富的69%,这些富人多为金融家、贸易巨头,而工业企业主财富大幅缩水。大量资金和技术的外流,使国内基础产业的升级换代变得艰难。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转向以金融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立国”战略,将“金钱游戏”发展到了极致。从1995年起,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超越了制造业,成为对国民收入和GDP贡献率最大的行业,到2008年金融业利润已占全美利润总额的40%。1995年11月共同基金资产额首次超过了银行存款总额,证券市场投资占到个人财富的26%,股票占到个人金融资产的50%,个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票份额到2000年达到48%。1997年时,最富的10%家庭拥有全国净资产的73.2%。财富的更加集中化,使美国经济与社会变得异常脆弱,在迄今仍在发酵的“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这五百年万花筒般的变换过程中,从来不乏清醒而理性的批评。1600年,学者马丁·冈萨雷斯就提醒当时的西班牙,真正的财富源于不断增长的农业和制造业,而不是贵金属代表的金钱增多。1688年英国驻阿姆斯特丹领事威廉·卡尔注意到了当时荷兰人丢弃了节俭生活的传统,从中看到了衰败的迹象。20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代表约瑟夫·张伯伦一再提醒:“金融业过度发展将会使英国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且不能够自给自足。总之,国家会变得‘富有而脆弱’。”“一个国家如果只充当‘票据交换所’的角色将很难存活于世。”
然而,这些理性的声音并没有阻止那些领先世界的头号强国走向将货币变为可交易商品、扭曲货币交换媒介本性的金融过度化之路,也就没有阻止被新兴挑战者超越的宿命。
中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已成为世界最大出口贸易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小私营企业主日趋艰难、纷纷转向资产市场投机性炒作的势头格外值得警醒。至少,应当始终将金融业放在支持产业企业生产性活动的方向上,工业制造业和商贸业始终是财富和国家强盛的基础,任何时候,去工业化主张都是危险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