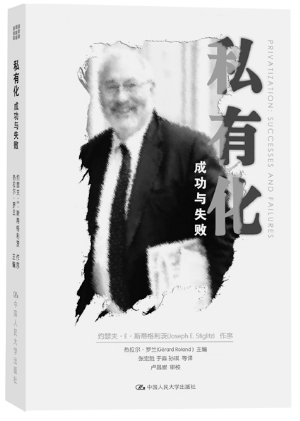|
——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著《私有化:成功与失败》
⊙潘启雯
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倡导,发端于英国的“私有化浪潮”,是20世纪末的世界经济大事。然而,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并未触及私有化,甚至连企业所有权问题都未曾涉猎。紧随其后的研究虽汗牛充栋,但当代经济理论在所有权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现实。正如这本《私有化:成功与失败》所示,“一种新的、更注重实际的共识正在形成。这种新的共识与经济学家常规表述的‘两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态势更加吻合。有些私有化获得了成功,但也有一些却铩羽而归,令人沮丧。而在公有制中,有的企业好得出奇,有的却一团糟。”于是,世人便面临这样的问题:私有化何时才能获得成功?各国该怎样做才能提高私有化成功的概率?
说起来,“‘私有化浪潮’初衷只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其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中欧、东欧等转轨国家也将其作为整改经济的灵丹妙药,卷入了这一浪潮。私有化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但更通常的情形是,绩效更差,令倡导者大跌眼镜,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乱。”
就私有化的收益而言,西欧位居全球之冠。在1972年至2002年间,约占全部私有化收益的三分之一。私有化收益较高的原因很多,较为明显的是,人均GDP高,股市规模大且流动性好;此外,也与高公债和低增长有关。后一组原因表明,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及经济绩效恶化的担忧,在催发私有化运动中也许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遵循“票高者得”的选举制国家,私有化动力较足。
有趣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左翼政府对私有化的热情并不比右翼政府更低。尤其令人惊奇的是,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在西欧体现得并不明显。唯一可信的证据是,私有化对公债具有负面影响。私有化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有关,也与企业层面较好的经济绩效不无干系。但这些经验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它们取自被私有化的企业和未被私有化的企业之间的绩效比较,而那些被私有化的企业,要么最能盈利,要么最具盈利潜能。迄今为止,那些能正确反映私有化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欧美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有趣发现是,“相当一部分项目(至少有30%)只是将国有企业的一少部分资产实现了私有化”——政府对私有企业仍然持有较大份额,似乎极不情愿失去对国有资产的控制。
中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所推行的私有化,场面最为壮观。欧美经济学家们坚信,私有化政策必须置于某国实施的转轨战略的一般背景下考察,包括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所扮演的相关角色、新生私有部门成长的相对作用等。围绕私有化问题,经济学家们界限分明地分为两派:一派靠赠送方案推崇激进私有化,也称大规模私有化;一派主张谨慎从事,渐进地出售国有资产。旨在实现各派主张的方案或文献可谓层出不穷。波兰、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等国采用了渐进式方案。俄罗斯、乌克兰、捷克、立陶宛,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斯洛伐克,实施了大规模私有化方案。实际上,两大派别只是粗线条的分类,具体实施方案在国与国之间差异很大。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献表明,最先私有化的都是那些盈利较好的企业。这种次序安排与私有化的政治经济理论相吻合:搜集支持证据以便进一步私有化。但令人不无诧异的是,私有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结果五花八门,多数研究是在私有化刚刚完成之后做的,而另一些研究又仅仅是依照公有和私有这种粗略的两分法来进行的,没有虑及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差别。受前期研究选择偏差的左右,是多数后期研究的通病。修正选择偏差后的研究发现,私有化对绩效的影响,仅居中等偏上的水平。由外国人购置国有资产,其私有化的效果似乎最为明显。
欧美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私有化在拉丁美洲国家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涉及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领域,直指微妙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分配问题。通常,一国只有当财政收入极为拮据时,才会启动基础设施私有化项目。由于担心政治上的强烈反应,通常采用租赁而不是出售资产的方式,也广泛地采用特许合同制。然而,当出现供电和供水短缺时,负面的政治反应还是发生了。在拉丁美洲,私有化成了筹集资金的一项有效手段。此外,总体上说,私有企业的投资流极为强劲。被私有化的企业的盈利能力获得了改善,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升。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受益并不明显,受益最明显的反倒是那些受监管的行业。为此,欧美经济学家们理性地指出,私有化对业已私有化的企业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为什么对私有化的政治支持近年来悄然消失了呢?一个原因是,尽管私有化形成了一个收入存量,但基本没有终结补贴和政府对有关行业的投资;另一个原因与收益的再分配有关,私有化为资产所有者创造了大量的租金,但普通公众却难以分享。
亚洲的经济发展态势强劲,但从来都不是全球私有化的“前沿地带”。南亚尤为明显。以印度为例,独立之后,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公有部门,也实施过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当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纷纷解体之后,印度加快了改革步伐。但印度私有化的成就并不显著,即使当前也只局部地剥离了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资产股份。尽管如此,欧美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大量证据,以显示这种局部私有化的积极作用。但金融市场容量有限、行政管理力不从心以及某些政治障碍,是限制印度私有化进程的三大因素。政治家不情愿私有化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政治赞助的工具。
亚洲那些近年来经济增长迅猛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并没有推行显著的私有化政策,但却释放了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家的生产能量,打造了一批既面向国内市场又面向国际市场、富有活力且蒸蒸日上的中小企业。因此,欧美经济学家们热切期待着,“国际金融机构能像以前关注私有化政策那样,关注这些小型私有部门的发展与成长”。
由来已久的政府失灵是“私有化浪潮”迭起的缘由。但私有化又引发了市场失灵。在某些行业,要确保私有部门与社会需要及期望相吻合,并非易事。因为“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定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而私有化过程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