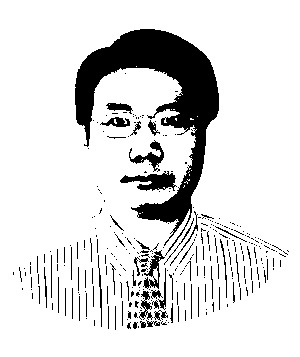|
袁 东
“论文,公道也。”这是那位18世纪才俊、“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言及文章时强调的。在他看来,公道不同于私情,因而,文章不是“家书”、“子戒”之类。
其实,公道与私情并不完全对立。公道者,若不渗入私情,难以引发共鸣,如此文章也就难以被广泛接受和流传。文章当然不是“家书”或“子戒”,但好的“家书”和“子戒”也可能是篇好文章。唯有面对家人子弟时,才是真心表述。私情最真。就是这位郑板桥,不也同样将他写给弟弟的16封家书,当作了一篇篇文章,并集成了《十六通家书》而广为人知吗?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恐怕更喜欢曾国藩的家书,而不是他的公道文章。
对美国金融业有着重大影响的J.P.摩根,给儿子的每封信也都是情真意切的好文章。后来,有人将其中的32封信件集结成一本书《摩根信札——财富巨擘给继承者的商业忠告》,这被认为“是一本培养伟大企业家无可比拟的教材”。
相比而言,郑板桥视文章有“大小乘法之分”倒是有道理的:“文章有大乘法,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谓。”大乘法的特征:“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哪些文章算是大乘法呢?“《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相比之下,小乘法者,一味“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捻断黄须,翻空二酋,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此真所谓劳而无谓者也。”
至于郑板桥一再强调“文必切于日用”,不能像宋明理学那样“执持纲纪”,否则,就“只合闲时用着,忙时用不着”。则未免过于偏差,可谓只知一面,不见另一侧。如果天下文章,都像郑板桥一再推崇的韩信获封大将军时的演讲,诸葛亮首次面对刘备时的“隆中对”那样,才是顶级的“切之又切”,就过于实用主义了。不要说一般的理论与思想难以存继和丰富,就是当时的韩信和孔明,也不可能有“切之又切”的言词。须知,实用主义的文章,恰恰是思辨性抽象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特别是后者,过于实用,就会看不远也走不远。
先秦之前,诸子百家的中国学说原本是虚实结合的。可是,自秦之后的近两千年里,中国学说大多以科举、兵法和政论等实用为主,始终缺乏形而上的理性思辨,致使中国的科学精神不足,进而在哲学、科学理论、技术进步以及艺术上被经过启蒙运动洗礼过的西方远远抛在了后面。而被后人认为趋向实用的汉学,就因为过于为形而下的具体考虑,反而最终走向借助超验的力量,试图去统合各种学说。作为突出代表的董仲舒,就在过于实用的促赶下,拿起“天人感应”的招牌,去为“独尊儒术”寻找学理依据,结果落入了反理性的虚妄之中。
相比之下,宋朝朱熹的理学,则有着理论上的气势,理学的抽象思辨,使得“处于散落状态、感觉状态”的儒学,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于是开始构建起了完整形态的儒学。在此基础上,经由明朝王阳明发展了的“心学”:“心外无物”、“心外无学”、“知行合一”,使“形而下”与“形而上”有了明确的界定,理学也有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大体轮廓。
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这种所谓“玄虚”,恰恰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少有的思辨理性学说,使过于形而下的具体实用感性,稍稍向形而上的抽象理论靠拢,正因为如此,这两位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典哲学家。在这一点上,可以套用袁枚的说法:“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
板桥先生所谓文章应避“一身一家之事”,而应专注属“天地万物之事”的忧国忧民,实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主张:重群体,轻个体,重纪纲与秩序,轻自在与本性,只有责任没有权利。这又与他那“文必切于日用”的主张相矛盾。但是,郑板桥的叙事方式和视角在中国历史上是普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连续而一体的,但越来越省略成偏重甚至只是治国和平天下了。总体上,这可能也是致使中国历史上排挤以至打击个人主义,学说学问缺乏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文化根源所在。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缺乏激励性,约束和压抑过多,社会的创新精神缺乏。
个人主义方法论,不仅是近现代哲学理性与科学理性的体现,奠定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基础与框架。个体,不是“单个数”,而是集体和“平均数”,若将个体当作集体的附属,当作无自在自由的木偶,甚至只是一种虚拟,那一定是令人生厌甚或十分疯狂的“假大空”。如此说来,“一家一身之事”正是“天地万物之事”的根源与归宿,只谈后者而不讲前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干瘪僵硬,了无生气。
时至今日,抽象思辨理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实在,以及两者如何结合,仍然是中国社会在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